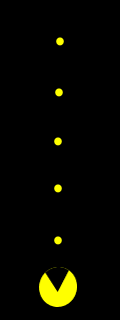文/小姜(新浪网友) 图/何智 欢迎网友投稿

我记忆中的女孩的名字叫鸭蛋儿。
这样的名字在黑龙江的那个偏僻小山村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个小山村我把它叫做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渡过了从两岁到十四岁的时光。鸭蛋儿就是我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记忆就好像是隐藏在某个角落里的水晶一样,不时发出一丝光亮。确切地说,那不是水晶,而是一滴永不干涸的泪水。
鸭蛋儿是因为长着一张秀气的鸭蛋脸才被她的父母和长辈叫这个名字的。她有没有大名,我不知道,但却从未有人叫过。我老是在想,即使鸭蛋儿有大名的话,那也只有她的父母知道。而自从她的母亲死了以后,父亲是否能够记得住女儿的大名,那也是令人怀疑的。反正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叫过她的大名。她从没念过书。
或许是受重年轻女思想的影响,鸭蛋儿的出生并没有给她的家庭带来多少欢乐,相反,她的父亲从来就没有给过她应该有的关爱。也许在她的父亲看来,能把她养大就已经足够了。反正将来是要嫁到别人家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是要跟别人姓的。他要的是个儿子。可鸭蛋儿的母亲自从生了鸭蛋儿以后就再没生育过。于是,鸭蛋儿的母亲作为女人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她成了鸭蛋儿的父亲的奴隶和打骂的对象。不过,作为母亲,她还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和爱着鸭蛋儿。尽管那份爱同别的孩子所得到的比起来微弱得多,可对于鸭蛋儿来说已经很可贵了。
好像鸭蛋的苦难是从她的母亲在她十岁那年死了以后真正的开始了。在那以前,尽管父亲不喜欢她,可她能从母亲那得到一个女孩子能得到的唯一的母爱。自从母亲死后,再也没有人痛她了。于是和母亲共同生活的那段时光成为鸭蛋儿最甜美的回忆。
那时,村里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们能上学的都上学了。上学,对鸭蛋来说是不现实的。鸭蛋儿的现实就是做家务。按她父亲的话是学做一个好媳妇,等将来嫁个好婆家,就算对得起她了。对父亲的决定鸭蛋儿从不说话。她已经习惯了。鸭蛋儿只知道从她记事起,父亲就是一家之主,父亲的话是不能违扭的。尽管父亲常常出去赌钱,赌输了就回来打母亲,还骂她,嫌她不是个男孩子。家里总是一分钱也没有,鸭蛋儿也就总是穿得打着厚补丁的衣服,可因为有妈妈在,总是干干净净的。
母亲死后,父亲更是不管她。她在家里做家务,还喂了两口大猪。这时候,她的衣服从来没有干净过。乡亲们每当说起鸭蛋儿的时候都是那样一种口气:“哎,可小鸭蛋儿啊……”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
时间是弥补所有伤痛的良药。鸭蛋儿也有伤痛吧。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她的母亲死的时候,她哭过。在这以后,没有见过她流泪。也许她对目前的生活已经麻木了还是她对目前的生活比较满足:自从母亲死后,父亲并没有打过她。
在鸭蛋十四岁那年,父亲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取了个女人。那女人还带了个弟弟来。那女人和她的父亲一样也是个不管天不管地的人,天天赌钱天天不作家务。于是,鸭蛋儿的工作又多了照顾弟弟和侍候继母。
但这并不能讨好继母。继母喜欢的是钱而不是鸭蛋儿。
可鸭蛋儿能换钱。至少我认为她是这样想的,要不然鸭蛋儿会那么早出嫁。
鸭蛋儿出嫁那年她十五岁。我记不清是周岁还是虚岁。
鸭蛋儿的男人是个快三十的光棍。鸭蛋的继母要了他三千元的彩礼。这个数目在那时的那个小山村里是大数目。这是鸭蛋儿在那个小山村创造的一个记录:彩礼最多。
下彩礼不多久,就定了日子办了喜事。
也许是鸭蛋儿的父亲觉得要补偿一下女儿,婚礼办得风光而热闹。那天,我也去了。记忆中所有到场的人都狼吞虎咽的吃肉,大碗的喝酒。谁也没提那个作了新娘的姑娘。
自那天以后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也没见她常回家,可能是婆家离得远吧。
如今,我离开那个小山村已经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在那个小山村的生活,鸭蛋儿那张秀气的鸭蛋脸就会活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小女子的遭遇总是能让我对传统观念下女性的命运叹息不已。那时是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女性的命运尚且如此,无法想象旧时代的妇女是怎样生活的。可想而知女性要想获得自己的独立和应有地位还需要漫长的历程。
本文章及图片版权归新浪网与文章作者共同拥有。未经许可,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