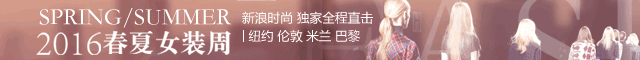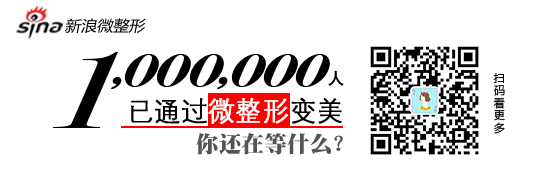近日,一位美国大妈荣黛佳和中国大妈一起跳广场舞的视频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五年前,美国人荣黛佳来到中国,由于语言不通和饮食差别等种种不适曾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生活挑战,但很快她找到了另一种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方式——跳广场舞。作为一名外教,荣黛佳已经习惯了乘地铁穿越大半个上海到原来的广场上找她的姐妹们跳舞。荣黛佳称自己的家乡小镇也有一个广场,如果以后回到美国生活,会非常愿意把广场舞带回跟其他人一起分享。
 广场舞
广场舞近些年,广场舞在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里流行起来。广场舞也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中国老人们特有的锻炼方式。在上海徐汇区交通大学的广场上,时常可见一个外国老太和她的“姐妹们”一起跳舞。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诗意的中文名,叫荣黛佳。近日,这位65岁的美国大妈和中国大妈一起跳广场舞的视频引发社会关注。
五年前,Debrah Roundy通过美国的“杨百翰大学中国教师计划”来到中国。初来中国时,荣黛佳“兴奋而又紧张”。位于爱达荷州的家乡小城只有5000人口,没有大城市的生活经验、语言不通和饮食差别等种种不适曾给荣黛佳带来了极大的生活挑战。
但荣黛佳很幸运地找到了另一种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方式——跳广场舞。此前,荣黛佳有过30年的教授芭蕾舞经验,这让她在看到广场舞后非常惊喜。“语言不通,就手舞足蹈靠比划,在一通鸡同鸭讲后,荣黛佳顺利地就成为了天平社区晚霞排舞队的一名新队员。”舞蹈队领队陈清娣阿姨介绍道。
荣黛佳和舞伴的日常交流,经常需要通过电子邮件、翻译软件来完成,而在跳舞中,没有了书面文字作为中介,荣黛佳就手把手教其他队员,还把芭蕾和美国乡村舞蹈等元素融入到了广场舞中。中西方生活经验和理念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给荣黛佳和她的姐妹们一些分歧。陈阿姨说:“我们中国人排舞和外国人不一样,我们是四个方向跳。她刚来的时候有些不适应,因为外国的舞蹈可能不像我们这样360度、全方位地跳,我们就1、2、3、4这样一点点去教她,她也很认真地学。”
陈阿姨回忆,有一次自己不在,荣黛佳和其他舞伴因为一些小事有了分歧,“其他人跟我讲说,荣黛佳就说‘no,no,no,听陈老师的’,因为在编舞排队形的时候难免会有摩擦,荣黛佳每次就说,那就听陈老师的。”
陈阿姨介绍,每年暑期,荣黛佳会回到美国,也会把广场舞带回去,“她会把中国的舞蹈展示给外国人,说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
另一位舞伴杨阿姨称,荣黛佳很喜欢太极拳、剑舞和扇子舞,“她每个动作都很认真,刚开始不会的时候,她会说‘重新开始’,让我们再教教她,也是逗我们笑得很开心。”
到中国后,荣黛佳先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教了两年书,后来到了同济大学成为一名外教。尽管换了一个学校教书,荣黛佳还是习惯乘地铁穿越大半个上海到原来的广场上跳舞,因为这里有她的姐妹们。
而在教课和跳舞之外,如今已到65岁的荣黛佳还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早起在地铁里给学生批改作业、做志愿活动、给朋友的孩子当家教、在社区教老年人英语等等,荣黛佳自称不愿意浪费任何时间。作为徐汇区天平街道天平居民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荣黛佳还被评为“2014-2015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
荣黛佳称自己的家乡小镇也有一个广场,如果以后回到美国生活,会非常愿意把广场舞带回跟其他人一起分享。
 广场舞大妈
广场舞大妈对话
荣黛佳:以前跳芭蕾舞 现在跳广场舞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联系到这位跳了五年广场舞的外国大妈荣黛佳,荣黛佳说起了自己的起名趣闻、来中国的波折和跳广场舞中发生的种种故事,一段段舞蹈和一曲曲音乐中的五年,也是荣黛佳融入上海,融入中国的五年。
刚来中国时最大挑战在于没有朋友
北青报: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当时为什么想要来中国?
荣黛佳:2012年9月我第一次来中国。以前我加入了一个神经语言学研究小组,其中一位在中国的朋友曾经跟我说:“你应该来中国教书。”但那个时候我还没退休所以就先拒绝了,但却对去中国产生了兴趣。
后来我联系了杨百翰大学,他们有一个“杨百翰中国教师计划”,也填了相关申请表。2012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我们收到了一封回复邮件,请我们去中国。
北青报:来中国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荣黛佳:像一场旋风一样,我和我丈夫迅速地参与了面试,并提交了相关的书面材料。我们通过后,就到杨百翰大学参加了培训。在来中国前基本上只有一周的时间收拾行李,因为之前我最小的女儿也生了孩子,我需要去她家帮忙照看婴儿。就在出发当天早上,我们还和其他家庭成员匆匆忙忙吃了顿早饭。在来中国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上海在地图的什么位置上,一切都是又兴奋,又有些紧张。
北青报:荣黛佳这个中文名挺特别的,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荣黛佳:我英文名叫Debrah Roundy,在希伯来语中,我的名字寓意是蜜蜂,我也很喜欢蜜蜂,本来想叫蜜蜂,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中国没有人会管自己叫“蜜蜂”,我觉得她说得也很有道理。后来她说可以起一个发音和英文名类似的中文名,就叫了黛佳。
北青报:来中国后,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荣黛佳:有很多,但我觉得更应该叫“挑战”而不是“困难”。上海是一座大城市,之前我和我丈夫都没有在大城市的生活经验,我家乡那边的房子基本上都只有两层楼高。另外就是找到我们喜欢吃的西方食物,中国有很多国外没有的蔬菜,很多朋友会来教我们怎么做饭。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在于没有朋友,但好在很快我认识了一起跳广场舞的同伴,也是姐妹,到现在我也交了很多朋友了。
北青报:在中国主要教什么课程?
荣黛佳:来中国之前,我已经当了40多年的老师,而且教过很多东西。之前我有自己的舞蹈工作室,而且教了30年的芭蕾。除此之外,也教过基础教育、特殊教育等,几年前我还参加了神经语言学相关项目。在中国我是一名英语外教,但不会要求学生们死记硬背,反而是学会怎么去和外国人交流、怎么去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等。
犹豫好几天主动提出加入
北青报:为什么当时你会选择去跳广场舞呢?
荣黛佳:我非常喜欢舞蹈,跳舞就是一种经历,通过跳舞也很快融入到了上海这座城市里,认识了很多非常好的朋友。
北青报:对广场舞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荣黛佳:来中国后,每天早上都会出门散步,但也会觉得孤单。后来看到了那些跳舞的女士们,她们向着蓝天舞剑,舞姿优美,每一个动作都很协调。后来她们还拿出了十分华丽的扇子,我们在爱达荷州从未用扇子跳过舞。我很想一起跳。犹豫了几天后,我才不好意思地提出请求加入,这些阿姨们也很支持我。
舞伴们就像姐妹一样 我们每周都在一起跳
北青报:你是怎么学习广场舞的?之前有没有跳过类似的舞蹈?
荣黛佳:之前从来没有跳过广场舞这种舞蹈,所以对我来说挑战也很大。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不知道舞步的名字,也不会说中文,所以只能在队伍后面仔细去看。有一天,一位舞蹈老师耐心地一遍遍跟我讲解舞步的名称,从那以后我也开始慢慢学到更多了,以后她们再说的时候我也能听懂了。现在一些名字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挑战,但是对用脑有好处。
北青报:一周大概会去跳多少次广场舞呢?
荣黛佳:平时学校有课的时候,基本上每周有三天在同济大学上课,有三天跳广场舞,还有一天会和“吃货小组”的朋友们一起玩。假期跳舞时间会更多,比如刚过去的五一节就都和姐妹们一起跳舞。
坐地铁专门去跳舞 感觉即使辛苦也很值
北青报:现在一般在什么地方跳广场舞?
荣黛佳:我在上海交大待了两年,后来转去同济。在同济,我到公园里转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很棒的团队。但现在还是会坐地铁回到上海交大的广场上跳舞,舞伴们对我来说就是姐妹。
北青报:同济和上海交大相隔也很远,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折腾?
荣黛佳:我觉得回交大广场跳舞也很值得,因为我每天都需要进行锻炼,早上步行去地铁站,这也是一种身体锻炼。而且我也会充分利用时间,早晨的地铁一般都有座位,我就在地铁上批改学生作业,而且也可以安静地好好阅读学生们的作业。
我和舞伴们用翻译软件聊天
北青报:因为语言沟通上可能有问题,你和舞伴们平时都怎么聊天呢?
荣黛佳:以前就是“传纸条”,我们在纸上写,然后我会拿回去给我的学生们帮忙翻译。现在好多了,我们用微信聊天,可以直接翻译,非常简单!虽然有的时候也不是尽善尽美,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聊得都很好。
北青报:在中国跳广场舞,很多队伍都会穿一样的服装,对此你怎么看?
荣黛佳:穿一样的衣服肯定有好处,也会有不方便的地方。我们穿一样的衣服证明我们是一体的,而且是平等的,没有人突出或者落后,这就是制服的力量。
当然有时候也不方便,穿自己的衣服会更舒服一些。我们跳完舞之后,大妈们也都有各自的事情去做,有些出去打零工,有些要照顾小孙子,所以穿自己的衣服会更方便。我们穿一样的衣服,而且化妆为观众跳舞,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谁出钱买了衣服,我曾经要付钱,但是她们没要。
北青报:除了上课和跳舞,你平时还会做些什么?
荣黛佳:我会在学校里面做志愿者,也会帮忙给朋友的孩子免费做家教。
我也会在天平社区做很多志愿活动,比如教英语、照顾孤儿、组织一些圣诞活动等等。他们很多人叫我“洋雷锋”,我觉得受宠若惊。
我为中国大妈设计“芭蕾版广场舞”
北青报:美国有类似的广场舞吗?
荣黛佳:我听说美国一些大城市有,也是中国的游客带到美国去的。很多美国大妈喜欢跳类似尊巴舞的舞蹈,和广场舞也比较像,但我更喜欢广场舞。
北青报:没有广场舞的话,美国人一般会在广场上做什么呢?
荣黛佳:在我们小镇里有一个广场,通常我们会在上面开一些派对啊、一起吃饭等,通过这些也可以增进大家的感情。
北青报:你之前也教过30年的芭蕾舞,那会把芭蕾舞融入到广场舞中吗?
荣黛佳:在跳舞的过程中,我也会把芭蕾的一些元素融入到广场舞中,尤其是其中有一个非常优雅而且漂亮的中国大妈,我特意为她编了一个“芭蕾舞版广场舞”。当我跳现代舞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想像成一个芭蕾舞者。
有时也会有分歧 最终大家还是听老师的
北青报:跳舞过程中,会不会因为东西方理念不同而和其他舞伴产生分歧?
荣黛佳:确实会有分歧,但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中外的差别,而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冲突吧。之前有一次我和舞蹈老师因为动作安排产生了一些分歧,很搞笑的是我们都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大家通过动作比划还都能明白。我当时也知道最后我还是会听老师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而且老师拥有最后决定权。
北青报:跳舞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语言或者文化上的区别,而发生一些乌龙比较有趣的事情?
荣黛佳:有一次跳舞的时候,因为其他舞伴不会英语,所以她们无意中选了一首歌词不太健康的歌,但是舞蹈动作编排得很可爱。我当时也很纠结要不要说出来,但好在后来没有跳这支舞,因为我也担心万一有懂英语的游客听到了这首歌,还以为这些跳舞的女士们都很淘气。
跳广场舞曾扰民 被人劝阻后决定“整改”
北青报:在中国,很多人也对广场舞存在意见,认为广场舞比较扰民,对这种看法你怎么认为?
荣黛佳:我们跳舞也确实遇到过扰民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妈们需要跳舞,但有的时候会吵到睡觉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来尽量平衡解决。
北青报:有没有遇到过因为扰民被质疑的事情呢?
荣黛佳:之前有一次是学校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们离开,因为怕吵到上课的学生,当时我也觉得有些难过。后来跟学校沟通后,决定以后尽量声音调小,而且要在早上8点前离开,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不断去调节。
北青报:广场舞一般都在公共场所中进行,但是跳舞又是一种个人行为,你怎么看这种公共和私人可能造成的一种冲突?
荣黛佳:这就需要互相融合,如果你在一个相对隐秘的地方跳舞,你可以把音响开到最大,也可以尽情跳舞。
但是在公共场所,还是需要考虑到很多方面,比如在我们跳舞的上海交大的广场,就有四支舞蹈队伍,我们需要经常控制好各自的音乐音量。而且为了不影响上学的学生,我们也必须早点离开。还有一些人会来问我那些跳舞的阿姨都去哪了,这些舞者还是很受欢迎的。
北青报:以后有没有回到美国的打算,会把广场舞带回美国吗?
荣黛佳:暑期回美国的时候,我也会跳给美国人看广场舞的样式,如果将来回美国定居,我也非常乐意把广场舞带回,和美国人一起享受其中的快乐。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郭琳琳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新浪女性(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