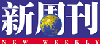裸给谁看 裸体表达的公众战争
导语:如今是个人表达至上时代,对于裸体表达者来说,随时可以以艺术或思想的名义对公众进行绑票,即使失败也将成为烈士,这是一场悲壮而稳赢的后现代战争。(文/林奇)
荷兰阿姆斯特丹东部的赫特伦小镇,“健康世界”体育馆在2007年3月4日举行了一场名为“裸体星期天”活动。十几位中年、老年人裸体在体育馆进行各种项目的锻炼。此次活动获得了荷兰裸体主义者委员会批准,但绝大多数成员表示宁愿参加远足或园艺活动,也不愿意来体育馆,也曾有女性报名参加,但最终没有现身。有趣的是,不少人关心的不是裸体的问题,而是卫生。
体育馆的会员表示很担心器械的卫生问题,有网友在体育馆网站上留言,裸体运动可以,但别在公共场所。活动中,这些裸体者被要求在举重器械上使用毛巾,在自行车等器械上使用一次性坐垫。活动结束之后,馆方对所有器械进行了消毒。
当地政府表示支持此次活动,称其能够促进居民的健康运动,而且裸体者有表达自我的权利。但如其他许多裸体表达活动一样,这次活动最终也只是丰富了报纸的花边新闻版面。
与国外的诸多裸体活动所遭受的待遇不同的是,在中国要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永远都会洋溢着悲壮的情绪。这仅仅是因为国情不同吗?
裸体反公众
屈原《九章:涉江》用了寥寥几个字描述了两位行为艺术的先驱者:“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这位桑扈兄为了表达对时世的不满,选择了裸体行走江湖。屈原对这两位显然心有戚戚,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位喜欢穿着怪异服饰的出位人士。
到了三国时期,一位“忠果正直,志怀霜雪”的祢衡在觐见曹操的时候,也大胆地选择了裸体表达。一曲悲壮的《渔阳掺挝》之后,祢衡先生施施然尽褪衣衫,他说得比桑扈兄更为直白:“吾露父母之形体,乃展示清白之躯耶”,直接针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趣的是,同为艺术家的曹操却并不认同他的艺术观和社会判断,满心不高兴,最终使用了阴险的小伎俩把祢衡辗转派到黄祖那里去送了命。
更不要说之后的魏晋时期,裸体成为了文化人、艺术家的重要表达方式。
裸体,向来是蕴涵着一种反社会的表达方式,裸露就相当于大声高呼“我反对”。问题是,反对什么呢?
2006年8月10日,在德国科隆,一帮动物保护主义者们裸体躺进保险盒,装扮成超市出售的肉制品,抗议人们食肉和残暴对待动物,他们的口号是“将你自己放在动物的位置”。之前的2006年6月,中国台湾地区的环保组织以“宁裸不核”为口号来抗议核电站建设,女学生在写满“核殇”的布上挣扎,最后挣脱,全身一丝不挂。Nuke(核能)和Nude(裸体)仅一字之差,在这里却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身体游戏。
这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众多裸体事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我们也可以想见,基本上,裸体所表达的抗议和反对都指向的是公共利益,尤其是自然环境。
当下的消费社会,推行的是消费拉动生产的价值观,以摧毁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乐事。现在的裸体人士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自掘墓穴的商业消费文化,这虽然同样是和社会主流需求对着干,但已经和桑扈、祢衡的古典裸体派对社会上层建筑捅刀子的行为大异其趣了。
裸体妄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肉体禁忌和表达需求,裸体表达虽然醒目,却并不一定清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2004年9月18日在圣塔克鲁兹市的裸体海滩上曾经有环保主义者组织过收集垃圾的环保活动。由于裸体海滩只有裸体者才能进入,这里的垃圾长时间无法清理,这帮好心人不得不全裸上阵——天可怜见,那天天气很冷,小风嗖嗖的。该组织发言人表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清理海滩垃圾,我们在裸体海滩清理垃圾并不是为了倡导裸体主义!”
可惜,这么善意、真诚地进入对方语境的裸体表达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裸体事件的全部。事实上,更多的裸体事件表达出来的意味却是走形、怪异,宛如谵语梦呓。
打算给自己出本书,于是就裸奔,还要奔遍全中国。“80后作家”向名主持人求婚被拒,于是发誓要“在她足迹所至的31个大中城市裸奔”。昆明出现“女体盛”,重庆就搞了“男体盛”,欲裸又不敢裸,几位女食客居然还煞有介事地表达了“有一种男女平等,挑战‘女体盛’的快感”。诗人要保卫另一个诗人或者保卫诗歌本身,于是毫无征兆地即兴裸体朗诵。至于更多充斥网络的女性博出位者,无不以裸露为最大亮点。
裸体本身与传统相对抗,裸体的实施者却利用了它这种反禁忌的力量感,成为自己有蓄谋的表达方式,也是最语义混乱的表达方式。后工业时代的裸体不再是表达方式,而变成了商业道具。
在福柯的逻辑里,身体分为“可理解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而对于那些居心叵测或者自己都一脑子浆糊的裸体表达者来说,只有“有用的身体”。我们的商业文明教会了这些人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体,身体在他们那里被商业所“规训”,成为用得最滥、最无趣、急功近利的表达方式。
裸体恐怖主义
1974年4月,在伦敦西部的特威肯哈姆体育馆举行的英法橄榄球比赛上,迈克尔·奥布莱恩闯入球场,他一丝不挂,唯有嘴角挂着一抹笑容。那张警察用头盔遮住奥布莱恩的重要部位的照片在今后几十年内成为了经典。纪录片《裸奔者》里,这位警官说:“那天很冷,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没什么可以自豪的。”
对于大众来说,裸体表达除了环保主义者的大义凛然,最为有趣的还是体育赛场上的这一幕幕调剂品。而我们不幸是中国的大众,中国的裸体表达者既没有庄严的普世主题,也没有趣味盎然的小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裸体表达是最缺乏幽默感的,我甚至怀疑他们先天就有着被迫害妄想,总是满腹怨恨。
首先,他们总会事先就把自己的表达和艺术联系起来。设立了这种前提,所有对其裸体表达感到不适的意见都会被自动归类为品位低下,严重的会被认为是阻挡历史潮流的道德卫道士。
其次,有一种观点认为裸体和性的联想意味着道德败坏和观念落后,再上升到民族性上,就会有5千个人向你举例鲁迅先生的名言:“看见白胳膊,就想起裸体;想起裸体,就想起生殖器……”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超链接的逻辑,对自己的表达不做任何自省和调试,却以道德观来划定观者。实际上,裸体的性意味从来就不是禁忌,也不是可以生硬切割的,夸张一点说,一个正常男性如果对于女性裸体不再视为性信号,不如去访问一下专科门诊。昆德拉在《笑忘录》里描述的那些男人也不过如此,“他们裸露的性器官这时正傻呆呆地、忧伤地看着地面的黄沙”。
如今是个人恐怖主义的时代。粉丝绑架偶像,我爱你所以你必须爱我;暴露胁迫观看,我裸露所以你必须观看。一旦裸体,则意味以艺术或思想的名义对你进行绑票,裸体表达者接管话语权,反对者势必遭遇道德家的恶名,表达即使失败,也将成为烈士。这是一场悲壮而稳赢的后现代战争。
网友评论 欢迎发表评论
- 伦敦数百人裸体骑自行车呼吁环保 2009-07-08 15:47
- 心理学家出雷人奇招:英国公司裸体办公提士气 2009-07-08 14:01
- 韩国裸体新闻因涉黄而倍受争议 政府对其亮红灯 2009-07-08 11:29
- 身体防晒Q&A 为全身肌肤撑起保护伞(图) 2009-07-07 12:07
- 口述:避孕!我的身体不是实验田 2009-07-06 20:59
- 视频:上海站现场速配情侣凝视着对方表达感情 2009-07-06 18:29
- 口述:为了4000元我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2009-07-06 10:56
- 最健康的身体才是最美的身材 2009-07-06 09:37
- 盘点颈椎病六大身体报警信号 2009-07-04 19:50
- 同租女心给了我身体给别人 2009-07-04 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