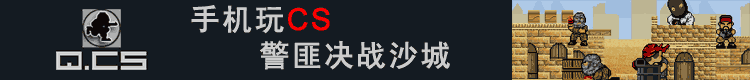像镜花,如浮月,记得起来的梦,是用来折磨和煎熬醒后的人生。那些为梦所趋使,栖身都市,投入一段热烈舞姿,再重拾从前每一夜的人,是妄为的。
佛罗伊德的理论,人的梦境是性思维的蔓延和性幻想的另一种方式的实现。
本地新开设了一家梦的解析诊所,专门对人的梦境进行分析和追根溯源。而解梦的房
间,有点类似与《无间道》中阿仁遭遇心理医生的那个场景:灯光是柔和的,音乐是催情的,窗帘和墙壁的颜色是安静的,问话是娓娓动听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个面对你的人,不是陈慧琳式的美艳女子,只是用倾听和关怀鼓励你平静下来并愿意述说。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也不愿意敞开心扉,把梦境交给眼前这些其貌不扬甚至有点严肃的陌生人。与其让他解开心中的迷团,不如把这个梦尘封起来。
春天的晚上,无聊并且多梦。临睡前的一杯葡萄酒,也无法让她一宵安静如水。
她梦见了十年前的一个旧人。
他是她男友的好友,所以,他们不可能牵过手,更没可能张扬地谈恋爱,至多也是在一个聚会上的惊鸿一瞥。他在音乐学院念作曲,住在上海幽静高尚的湖南路。夏天时候,她男友带她走进他家那条安静的,深不见底的弄堂时,总有某些琴声从某个被梧桐树叶遮住的窗口飘出来。
这是她对优雅生活的最初印象。
他总是穿干净的白衬衫,把自己打扮地一尘不染,像少年罗蜜欧一样的眼睛,在她看来是忧郁迷茫的。他们在他家坐整整一个下午,喝汽水,听他弄来的进口唱片,或者他弹他作的曲子。她知道她不是朱丽叶,虽然十分迷恋他,却无法让他为她歌唱。那一两年里,他组了一个乐队,在各地巡回,上电视台演出,在电台做节目,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每次看到他在电视里飞扬长发音乐激扬,总是忍不住的,像一个中年人一样的,唏嘘不已地怀念起当年的那些下午。
她就在春天的一个晚上,毫无预兆地梦见了他。已经十年过去了。她都无法把他的脸拼凑完整,印象中,他是有一个如龙泽秀明式的俊美轮廓和黑亮眼珠的年轻人。
七转八弯地找到了他的电话,用一个听上去无法拒绝的借口,约他周末晚上,在茂名路的酒吧见面。
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那天晚上见面的情形。那晚以后,她仍一如往昔地上班、下班、吃饭、逛街。只是在很久以后,她发了一句话在博客网的个人网页上:“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像镜花,如浮月,记得起来的梦,是用来折磨和煎熬醒后的人生。那些为梦所趋使,栖身都市,投入一段热烈舞姿,再重拾从前每一夜的人,是妄为的。
相见还不如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