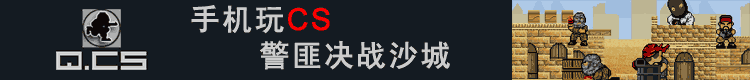文/林文杰
我们便成了同学中第一对结婚的人。盛大的酒会上,所有能找到的同学都来了。结婚当天在选婚纱时,我接到了余可的电话,他隔着千山万水祝福我,并放了一段刚编录完的音乐给我听。我的眼睛湿润,想起那段仓惶、迷茫的霍乱般的青春。
最后,我听了余可的建议,选了一条象牙白的缀着草绿色叶片的婚纱。
几年来,凯文的公司蒸蒸日上,搬了新的办公楼,有了固定的客户,并且涉足于时尚圈,做了很多国际品牌的大型时装秀。我离开杂志社跳槽去了一家跨国消费品公司做市场推广,一直勤奋地在这家公司里做了四年,职位节节上升。
我们俩经常天南地北地飞,聚少离多,家里冷冷清清,连我们最爱听的CD上也落满了灰尘。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日常生活的沟通,譬如该付水电、电话费了,该到洗衣店取衣服了等等;通过明信片确认对方目前已到了某一个城市。生活在我认为的有序的、平静的方式中延续着,直到那天在酒店里遇到凯文和那年轻女子。
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远行。凯文又去出差了,他不知道我要出去培训半年。桌上的明信片堆积如山,最近的一张,我知道凯文在香港谈一个品牌的上市活动。
那个星期里,我整理着行李,同时也想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从头开始。我还喝了很多酒,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话,写在一些用过的明信片反面。
我写道: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来梳理一下了。又写道:半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如果想清楚了,我们再坐到一起做个决定。诸如此类的字句。
临走前一天,凯文突然回来。他已经打过电话去我公司并且知道我明天就要到英国的事。
他看我的眼神变得很陌生,我突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什么时候决定的?”
“一个月前。”
“哦,最近我太忙,很多CASE在谈。”
“我早就买了红酒,想和你一起庆祝的。可惜,一个月来都没有机会和你喝一杯。”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好好照顾自己”。凯文回应我。
这一瞬间,我知道我们完了。
当晚,凯文留在书房里到很晚。翌日夜晚,我上飞机前,看到凯文放在我行李箱内的一个蓝色透明袋子。
我想起这个透明袋子还在我的手提包里,起身从行李箱中翻出来。
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都记录了一个日期,在右上角贴邮票的地方,贴上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旧照片:大学校园里我演出的剧照、放烟火时张嘴大笑的模样、毕业时草地上的留影、婚礼上一帮同学高声的欢唱。
明信片以记录的方式,把我们认识至今的一些有趣的经历,一些转折点和一些值得纪念的事,都配着照片完整地保存下来。大概有50多张。凯文种情于这种方式为我们的感情做着收藏,包括从前我无心说过的一句话。
我翻到最后几张明信片,一张右上角贴的是那晚和他一起在酒店的模特儿的照片,旁边写着:“她是我们同学小刘的妹妹,刚来上海发展。我答应替小刘照看她。其实那天我看到你出去打我手机。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和我沟通。你选择了毫不在乎,而我们却越走越远。”
另一张是临走前一晚他写的,照片上是那年12月31日的烟花之夜,只有一句话:“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而我们已飞过”。
飞机越飞越高,窗外漆黑一片。可是我知道有云朵飘过我的窗前,只是夜太黑,我无法分辨。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的那一段了。只有这一张张的明信片,像是手指划过皮肤留下的痕迹,仿佛还在不断地提醒着我: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嘉年华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