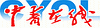一个地震孤儿和她的新家
“我来带路”,9岁的何元丽穿着凉鞋,与表姐蹦蹦跳跳地走到了队伍前面。后面跟着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和几名记者。
路夹在了大片白墙蓝顶的板房中间。正是做午饭的时间,到处都是锅铲接触锅底的声音和混杂着的饭菜香味,烟雾缭绕在过道间,有些呛鼻,一闻就知道是烧柴火产生的。狭而长的过道上,有人在摆“龙门阵”,有人在吃饭,有人在修自行车。
这片板房旁边是个喧闹的工地。在这块满是高山大壑地无三尺平的土地上,这片不到1平方公里见方的平地紧邻着一条小河。新规划的青川县关庄镇建筑工地热火朝天,林立里的钢筋水泥柱子已有1丈多高。
“到了!”何元丽回头喊了一句,充满川味的声音里满是清脆。
她推开上面标着“寺025”字样的房门,男主人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看到有人来,马上翻身起来招呼客人,脸上满是笑容。
“这是我舅舅”,何元丽向来人介绍说。
男主人赶紧拿过一包烟,用左手夹在腰间,忙不迭地伸出右手向每一个人敬烟。
房间里惊人地拥挤和杂乱:两张床一张桌子,占了房间的大半面积。大床上,被子和衣服占据了几乎一半的空间。这些衣服,有些用蛇皮袋装着,层层堆垒,直到紧贴着天花板,有些则胡乱地叠着搁在床上,堆了大半米高。桌子上,堆放着电视机、电话机、台灯、笔桶、梳子、水杯、牙膏等。做饭的煤炉摆在了进门口的左边,锅碗瓢盆却散放在屋子的各处。
随后进屋的女主人窘于房间的凌乱,一边找凳子张罗客人坐下,一边不自然地笑着说:“太乱了!太乱了!”
屋子的乱与人口密度有关。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住着两个大人三个小孩。
男主人叫王永先,女主人叫沈丽洁,本有一双儿女的他们,在去年地震后有了第三个孩子——何元丽——王永先妹妹全家六口唯一的遗孤。
何元丽突然从屋子的一角翻出一本大相册,一边翻,一边用手指点着某张照片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妈……这是我爸,这是我爸……”。
相册的一张照片上,一个脸蛋微圆的妇女,穿着红毛衣,扎着丝巾,手臂戴着罩袖,脸上满是恬淡的微笑。她站在河边,河对岸是一尊巨大的石佛。
另一张照片上,3个男子中,一个面色黝黑、留着中分头、穿着略显皱揉西装的年轻人,是何元丽的爸爸。这张照片是在广州拍的。
何元丽原本也住在东河口村,但那里正好处于地震波四大喷发点上,是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整个村子死亡和失踪共780余人。
沈丽洁说,何元丽的父母原本在广东打工,但2007年年底,妈妈给她生了个弟弟后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爸爸何显斌也恰好赶在地震前回家探亲。结果,何元丽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不满1岁的弟弟,全被村后牛圈包山蹦下的土石淹没。
而那天何元丽正在上学,她所在的东河口小学偏居村落一隅,被一座没有崩塌的小山头掩护,学校才整体幸免于难,但由于校舍倒塌,103名师生中,仍有3位老师和3名学生遇难。
地震后,与东河口小学大多数幸存学生一样,何元丽转到了临时搭建的关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由几间板房组成。原本该上三年级的她,由于地震造成的耽误,又上了二年级。
负责照顾她的,是住在与临时关庄小学同处一片板房区的大舅。
王永先说,地震对孩子的刺激非常大,他刚把何元丽接过来时,何元丽身上有多处被瓦片石块弄破的伤口,而且伤口多集中在背上,以致晚上不能躺着睡觉。大震过后,又是余震不断,何元丽会常常流露出恐惧、伤心的神情。
在地震中罹难的父母和爷爷奶奶,是谁也不能提的话题禁区。如果谁提到他们,何元丽一定会以难以收场的哭闹而告终。
而梦魇也没有放过这个小孩,她经常会在噩梦和惊悸中惊醒,一旦惊醒,就会哭着喊着要爸爸妈妈。
沈丽洁说,何元丽本是一个爱打爱闹爱说爱笑的孩子,但这场变故一度让她变得沉默而自闭。后来,志愿者来了,陪她聊天,跟她做游戏,她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重现了原有的天性。
网友评论
- 生了孩子后男人就变心了 2009-05-12 11:39
- 视频:盘点娱乐圈十大个性妈妈 2009-05-12 10:58
- 视频:陆毅鲍蕾勤俭节约 为孩子教育存钱 2009-05-12 09:40
- 官员被女服务员用修脚刀刺死 据称其用钱打女方 2009-05-12 09:40
- 英调查:父母太放纵使肥胖孩子多(图) 2009-05-12 08:47
- 麦当娜:想当妈妈不容易 2009-05-11 14:20
- 视频:董洁陶虹大谈妈妈经 2009-05-11 09:51
- 口述:我把孩子藏起来 惩罚丈夫的不忠 2009-05-09 20:45
- 孩子眼中的那场出轨事件 2009-05-08 21:09
- 口述:情夫和他老婆抢走了我的孩子 2009-05-08 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