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更有智慧地做慈善
阅读提示:杨澜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密,在采访结束后,马上就要到上海世博会参加中国馆日节目的彩排。但对于慈善的话题,她侃侃而谈,和记者分享了她在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慈善晚宴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她对于慈善事业的所思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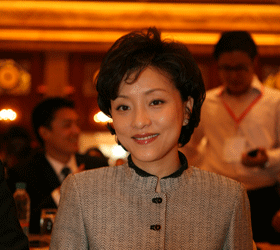
更想谈的是捐给谁、怎么捐
《环球》: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到中国开展“慈善之旅”,推动慈善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他们此行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的?
杨澜:这一次我也觉得非常荣幸,因为我的阳光文化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一道,作为共同主办方,来策划和主办这一次的慈善活动,我觉得它对于中国慈善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两位大慈善家来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慈善理念和经验。同时他们对中国慈善环境的好奇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反省的过程,考虑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益。
我觉得在这之前,似乎中国的媒体和公众的兴奋点是在谁捐、捐多少,我们这次交流活动其实更想谈的是捐给谁,怎么捐。盖茨先生和巴菲特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就是如何更有智慧地来做慈善。这种智慧就是,虽然慈善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它同时也有性价比的考量。你同样付出一笔善款,究竟哪一种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益呢?
比如说你想捐出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是给路边的一个乞丐好呢?还是给一个要上学的孩子好呢?是给一个病人好呢?还是给医疗机构去研发治疗这种病的疫苗好呢?所以慈善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并不一定有这种高低之分。它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性的选择,但是我们过去在慈善的效率和效应方面的思考显然少于对于意愿方面的考量。
《环球》:有富豪表示将在离世后捐出个人全部财产。慈善的形式多种多样,无法对其进行单一标准的评判,但就其示范意义来讲,你认为这是否会成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一剂催化剂,会对中国的慈善事业起到怎么样的积极意义?
杨澜:我认为这种现象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并不一定是一种最好的回馈社会的方式。因为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通过公私合营和国有化的浪潮把所有当时的民营机构全部都国有化了,消灭了民间的资本,在这之后是不是实现了全民的富裕呢?并没有实现。而中国的民间资本真正的积累不过才刚刚30年,而且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民营企业承担了80%的重任,也就是说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而且这些企业本身都还在一个高速成长时期,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企业家把所有资本从一个有效运转的、为社会提供可靠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很多就业机会的企业中抽离出来?
这就有个前提条件,抽离出来的资本是进入了一个高效运行的慈善机构呢?还是投入了一个低效的、不透明的、甚至是有可能产生腐败的慈善机构呢?那么他们会产生的效益是需要具体地来分析的。所以呢,我觉得有关“裸捐”的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关捐款意愿的讨论,而不是关于一个捐款效应的讨论。
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更应该来关注我们怎么样让慈善变得更有效,也就是说,我们的受益人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的一笔慈善捐款是为了让穷孩子们能够上得起大学,那么我们就要问,若干年以后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只要考得上大学都能够上得起大学呢?要有一种社会评估体系来衡量这种慈善行为的效果。
“诈捐”大多并非恶意
《环球》:此次“慈善之旅”是否会在官方层面引发对慈善体制的思考?例如改革税制,加大对捐助行为的鼓励,或是完善对慈善机构的管理?
杨澜:这也是我们的慈善晚宴与这两位先生过去在美国的慈善晚宴不同的地方。他们在美国的晚宴,的确是只邀请了一些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家人来参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既邀请了财富榜上的企业家,也邀请了慈善榜上活跃的慈善家,同时我们邀请了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大型国企的老总,以及民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我们就是觉得在中国做慈善是需要多个阶层的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某一群人的专利或者特权。
那么说到中国慈善发展的瓶颈,我觉得有两个,而且我想这两个都引起了到会的民政部高层官员的注意。一个是我们需要制度性的突破,特别是我们希望尽快出台“慈善法”,就慈善的规范能够有明确的规定;第二个瓶颈是现在慈善机构的专业化程度明显不足。那么,当慈善机构非常弱小、资金能力不强的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慈善愿望和捐款意愿。
《环球》: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公益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同时也引来了多方的监督,“诈捐”无疑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现象,尽管大多事后得到了澄清,但这在一定角度上反应了公众对目前公益募捐的些许质疑,对此,你认为除了加强适当的、必要的监督机制之外,还应做哪些更有建设性的工作来推动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同感?
杨澜:我觉得以往出现的几次所谓“诈捐”的事件,如果具体分析一下的话,大多并不是恶意的“诈捐”,而是出于良好的意愿认捐,但是由于后续的跟进没有跟上,而出现了跟公众的期待有了落差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当事人要把公众的捐款收为己有,我想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由于团队疏于跟进,作为当事人,过一段时间又会忘记,从而引出这种尴尬的局面,可能这个还是目前大家遇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呼吁专业的团队来做专业的事。
比如巴菲特先生在慈善晚宴上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如果我要去拔牙,我一定不会自己拿着钳子来做这件事,我一定要去找一个有经验的牙医。我觉得比尔-盖茨做慈善比我做得好,所以我把这笔钱就交给他去做,我要知道我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如果很多名人、明星还是抱着“我捐的钱、自己的团队去执行”这样的比较初级的理念的话,那可能就很难保证操作的专业性。而且我也不是特别赞同企业家自己拿着现金跑到灾区去,每人手里塞几百块钱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也很难衡量。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建设让慈善机构变得更加专业,那么我们可以放心地把钱给他们,而且他们要告诉我们这钱要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先生这次来到中国,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在美国,如果要捐钱,你只要愿意捐就可以了,因为有数量庞大而且是相对效率比较高的很多非政府组织来执行这些善款。但是在中国,公益组织相对地都比较弱小,专业程度相对都比较弱一点,所以不是你捐款意愿有多大的问题,而是说这些机构能帮助你执行多少的问题。
慈善重在可持续
《环球》:你认为中国社会最需要怎样的慈善文化?
杨澜:我觉得中国的慈善文化处于一个刚刚开始高速成长的阶段,正是蹿个儿的时候。我希望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是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它不仅是非常地茂密,而且是种类、层次都比较丰富,互相作为补充的。就像一个企业,它不可能包打天下,它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慈善机构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比如说,在四年前,我们阳光文化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考量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资金,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决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慈善文化的推广,还有进行慈善的能力培训方面。因为这几个方面我们具有资源上的优势,而且可以做得更好。而没有去选择把重点放在救灾或者是扶贫这样一些同样也是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我们特长的一些领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慈善需要全面的发展,同时需要各个慈善基金会找到自己非常明确的、在各自领域的定位。
《环球》:国内慈善事业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你认为各个慈善机构应如何完善自身的发展模式,更务实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优质的慈善服务?
杨澜:我觉得首要一点就要有明确的定位,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我发现很多的慈善机构还是属于“From Hands to Mouth”的模式,直到有了进项,才知道往哪儿出。刚刚“化缘”来一点儿钱,马上就花掉了,缺少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规划。
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的捐款热情最高呢?救灾的时候。但是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社会,救灾就是政府该做的事,民间机构反而很少去做救灾的事。那么,更多的民间机构在做什么呢?是教育、艺术、科学研究、宗教,这是几个最大的捐款去向的领域。所以美国的公益和慈善机构,是在某一个领域做得很专业,而且很长久,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而我们的很多公益机构,在大灾之年的时候,捐款就会上升一百倍,但是在没有灾的时候,他们日常的维护都显得步履维艰,这样一会儿饱,一会儿饿的状态,很难保证机构会长期运作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慈善的状况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不可预期的,而且是跟随一些偶然事件上下起伏巨大的这样一种现状。而在一些更加成熟的社会当中,它应该是相对平稳的,无论是公益机构,还是普通的捐款人,可能每个月就捐10美元,但是会一辈子都这么做下去。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有灾时,会捐一万元,而平时可能不会去捐钱。所以这种慈善环境和氛围是不一样的。
《环球》:所以,像李连杰的“壹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倡议?
杨澜:对,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的参与比募来多少钱更有意义。我同意他的这种观点。我觉得慈善事业的发展不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小群体的权利,应该有一种全民参与的机会。
慈善不是快退休了才做的事
《环球》:你认为慈善机构应如何扩大自身以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杨澜:我觉得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包括专业人员进入到慈善领域,这个方面的呼吁已经越来越有力量了。像阳光文化基金会今年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我们请到在世界著名的公司当中任高管职位的商业管理人员,拿出他们的业余时间做一个志愿者,来与公益机构的管理人员交流管理经验,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互动也是一种慈善形式。慈善应不拘泥于某种特别的形式。不过,可能各个慈善机构共同呼吁的,就是中国“慈善法”的早日出台。
《环球》:慈善是全球性的事业,但各国管理机制不尽相同,你认为何种机制适合中国慈善发展的趋势?
杨澜:我举几个普遍现在困扰基金会的例子来说明吧,我认为在“慈善法”当中应该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才能让大家不至于迷茫。
比如说,第一,捐赠有价证券能不能被认定是捐赠。比如说一个企业家把自己的公司上市了,他把自己的股份捐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那么按照现在的基金会的管理条例,是必须要把这些股票兑现了以后才能够算作捐款的。但是同时,证监会也要求你不能一下子把自己的股票变现,因为这个会对股市产生重大的动荡。但是你回头去看,巴菲特、比尔-盖茨他们的捐款主要就是有价证券,巴菲特并没有把自己的股票都抛售套现了,才把现金都交给比尔-盖茨。而实际上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是有两个机构,他左手是捐钱的,右手呢,是一个资产管理的机构,每年还要负责进行投资,来获得分红或者收益,以便维护整个基金会的正常运转。所以他还要有个投资机构来保值增值。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立和你如何来认定它们的性质,这个是需要法律做更明确规定的。
第二,目前基金会当中,当你吸收了善款,而这笔善款第二年产生了一个增值的话,那么增值的这个部分是要被课以企业税收的。有一些企业家就会说,我这钱已经捐给慈善基金会了,怎么每年的收益你还按企业的标准来收税呢?这是不是公平呢?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有待于解决的。
第三,究竟什么样的基金会能够获得相对独立的公募的资格。前一阶段李连杰先生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苦恼,因为他希望成立一个不用挂靠在任何基金会下边就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而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这个口子是没有开的。所以,大多数的公募基金会,它都必须要挂靠在一个有公募资质的大基金会的法律和财务管理之下,才能够运作,你不能够独立运作。
为什么大家都希望有制度性的突破,因为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法律的层面给予清晰的界定。当然政府部门也会有一定的困惑,比如说,如果要是有价证券捐赠都可以免税的话,会不会有人在这里洗钱呢?会不会有的人逃税呢?我觉得作为国家就要权衡。这种逃税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与给社会做公益的这样一个正面的效益相比,孰重孰轻呢?当你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风险的时候,这个风险值不值得呢?也不能有这样的风险就完全不做,对吧?对于这些问题,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
《环球》:这是逐步完善中国慈善事业的必经之路。
杨澜:对,其实美国也是花了几乎百年的时间才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慈善法的。它一开始做的慈善法也有一些漏洞,成为逃税、洗钱的一些场所,但是后来不断发现问题,就不断来修正,所以现在它的慈善立法相对是比较完善的。
我觉得比尔-盖茨这次提出的一个理念非常好。他说,过去常常我们要在退休了,或是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想起来做慈善的事,其实,慈善是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慢慢做起的、不断积累经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慈善什么时候做都不嫌晚,但是早做更好。
- 花边报:万圣节进行时 明星变装大比拼 2010-10-29 17:11
- 巴黎巧克力展开幕 时装秀明星助阵 2010-10-29 15:04
- 新年新开始 明星转运从发型开始(组图) 2010-10-29 14:55
- 秒杀过我们的明星销魂美照 2010-10-29 10:28
- 视频:《骇时尚》好莱坞最富魅力的三大明星 2010-10-29 09:43
- 明星约会最佳妆容 富二代最爱(组图) 2010-10-28 2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