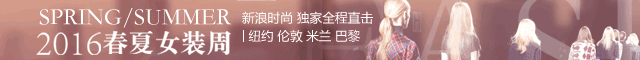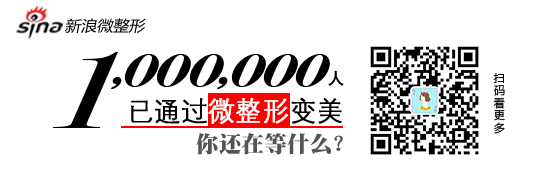5月19日,爱穿裙子的女生谢仁慈,遇见同学总是微笑着打招呼。
5月19日,爱穿裙子的女生谢仁慈,遇见同学总是微笑着打招呼。 5月18日,民法考试补考前,谢仁慈在抓紧时间看书。
5月18日,民法考试补考前,谢仁慈在抓紧时间看书。谢仁慈头发齐耳,爱笑,她走路很快,右腿几乎不弯曲,短裙下蓝色的金属假肢骨架随着惯性向前甩动。
5月17日中午,西南政法大学附近,她身着短裙,路过一家酒店大堂。一名妇产科医生看到她,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医生面前的女孩和那条热门微博里的女孩一样,右腿装有“撕掉包装的假肢”,也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嘴角旁那颗痣,伴着笑容在唇角起伏。
确认了谢仁慈便是微博中的“截肢女孩”后,她们合了一张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一周前,这位妇产科医生为一位孕妇胎检,发现胎儿有足内翻,纠结许久,建议对方拿掉。后来,看到谢仁慈的微博,转发给产妇,让对方再考虑考虑。
分别后,谢仁慈和三个朋友分享了这次偶遇,她有些感动,声音微颤,“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有点用了”。
“西政的太阳”
5月12日,她在知乎上被朋友邀请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穿短裙把两条腿的假肢露出来,走在大街上会怎样”?
一晚上,她的回答点赞数破了五千,后来涨到两万六千多,她的微博被人找到,粉丝从二百涨到两万多。有人评价她是“西政的太阳”。
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什么太阳,简直是给母校蒙羞”,她不想变成一个励志典型,只想讲自己的故事。
三年前,她考上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在这座被人称为“山城”的城市上大学,她上一次课需要爬近200个阶梯,翻过好几个山坡,中途休息四到五次。
入学第一年,她总摔跤,每到下雨,伤口疼到几乎没法出门。这个短发女孩大学第一次逃课,是因为爬坡爬到一半崩溃了,她给朋友打电话哭诉,“我实在是太累了”。
如今,和她一起走路的同学,总没她快,谢仁慈能快则快,“因为走路磨伤口,想把痛苦的时间尽量缩短”。
谢仁慈生长在一个并不如意的家庭——父亲和人打架打到需要“把他的肠子往肚子里面塞”,常年在外坐牢;在一次车祸中,母亲和她一样,成为残障人士。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天天吃面条,她问母亲为什么,母亲哄她,因为面条好吃。
刚上大学时,母亲凑不齐学费,谢仁慈申请过贫困生助学金,每年2500元。大二时,家里条件可以支撑她正常生活后,她再没申请过。
这个总说自己上了大学变得懈怠的女孩对自己要求并不低,去年她有三门学科没考好,都在75分左右,她全部选择了重修。
谢仁慈在知乎上那张被人赞叹的健身照片,是朋友无意间拍下的。学校健身房内,她存有专门用来健身穿的假肢,比平时的更重些,骑动感单车不一会儿便会出大汗。
一位副教授曾在健身房偶遇她,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在健身房看到一个小姑娘,她一条腿戴着假肢,不断尝试各种健身器械……我问她,你为什么推哑铃?这个20岁的小姑娘咧嘴笑,大声说,为了防止胸部下垂。
 5月20日,谢仁慈在健身房练习平衡。
5月20日,谢仁慈在健身房练习平衡。车祸
2001年3月21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谢仁慈穿着裙子、红色小皮鞋,跟着母亲出去玩,走到一家诊所门口,看见医生在给别人打针,吓坏了,扭头就跑,伴随着剧烈的刹车声、母亲的叫喊声,这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被大巴车卷入车底。
睁开眼睛时,她眼前是汽车底部黑乎乎的、交错的零件和管道,鼻腔中充溢着燃油味,热气蒸腾,脸被熏得很烫。
关于车祸的记忆没有痛感,她只记得,自己茫然地睁着眼睛,被人拖出车底时,大巴车上有位中年男人往下看,对方头发很短,十六年过去,对方神情里的漠然,至今难忘。
母亲为了拉她,也被车撞了。这场车祸,女儿失去了右腿,母亲失去了左腿。
打车前往医院的路上,谢仁慈低头看到自己的右腿,膝盖往下,黄色、青色、红色交织,经脉、血管、肉纠缠在一起,晃晃荡荡。
母亲止不住地哭,她清楚地记得,计程车司机用方言说,“别把血滴在我车套上”。
母亲没有反驳,抱着她不停念叨,“崽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车祸时,谢仁慈只有4岁。那时,这个苗族小女孩能跑能跳,还被同学们选去做“校园主播”。
车祸过后,她在医院待了三个月,母亲住六楼,她住五楼。爱穿高跟鞋的母亲总是做噩梦,梦见医生在手术台上说,“这个锯子不快了,要拿剪刀来剪”,然后惊醒,大哭,想从六楼跳下去。
谢仁慈知道母亲难过,每天早上打完针后,自己搬着小板凳,左腿着地,用双手撑着,一步一步跳到六楼,磕磕碰碰,去找妈妈。
“我不安慰她,只跑到她身边去,黏着她,脚跟脚。”
一天夜里,母亲看着她趴在床边,对自己说,“要用所有时间,陪孩子走完,扶她长大。”
两年时间内,母亲教她读拼音,学汉字,每天七点半之前背乘法口诀,背不出来就挨打,还未念小学,谢仁慈已经可以把一年级的课文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
残障儿童很难就读普通学校,母亲四处求人,拄着拐杖,一天问一个学校,“可不可以让我女儿去读书”。谢家老宅旁边有一座桥,谢仁慈每天傍晚都在桥边等母亲回家,看着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低着头回来。
“学校都不要你,不然咱们就别读了吧?”
“妈妈我想读书,你让我读书吧,我……我一定会考上哈佛的”,一听到不能读书,谢仁慈眼泪就掉下来。母亲也哭了,“好,妈妈再去问问”。
后来,一位小学校长答应收下谢仁慈,母亲专门把家安在了学校附近。一到放学时间,母亲就在路上等她,并规定谢仁慈:到时间你就要回到家,没回来,我就打你。
打得厉害了,奶奶骂她是“后妈”,母亲从不辩驳,“现在我能打,我就打,我怕她会步她爸的后尘”,每次女儿挨打,母亲都会哭。
 5月19日,路过的市民,竖大拇指,为谢仁慈叫好。
5月19日,路过的市民,竖大拇指,为谢仁慈叫好。假肢与自尊
车祸后的谢仁慈,感觉到了自己的“不一样”,用厚重的壳把自己包裹起来。
二年级时,她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追赶游戏,跑太快了,假肢飞出来,所有的小朋友开始哇哇大哭,一哄而散,她自己爬过去把假肢捡起来,一瘸一拐地挪回家。
她变得越来越坚强。附近有男孩骂她“瘸子”、“铁拐李”,她直接和人在菜地打了一架,“困兽之斗”,尽管对方咬住了自己的手,她还是把别人打出了鼻血。
从此,附近的男孩子叫她“仁慈姐姐”,谢仁慈成为贵州“三道河一霸”。
很长时间以来,她的人生信条都是:生活已经挺难的了,还记着别人对我不好,还活不活?那些所谓“被伤害的故事”,她几乎全忘了。
印象最深的是高二那年,她是班长,班上同学都在准备“校园舞会”,她在图书馆看书,“没有人问我跳不跳,他们都觉得我不能跳。”
那天,她坐在图书馆,耳边都是校园舞会的歌声,哭了。
十几年时光里,她从没穿过短裤,把假肢包裹在暗处,“藏得越深越好”。那时候,她在意别人的眼光,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假肢脱落,自尊跟着一起被摔碎。
她见到身边人,会把“我好喜欢你”挂在嘴边,有朋友评价她,为了自我保护,善于察言观色,“见着谁都会摇尾巴”。
情绪反复挣扎时,她疯狂读书,看周国平、余秋雨,也看康德、卢梭、萨特。
离高考只有一年时间,谢仁慈的模拟考试成绩只有400多分,她感觉到了紧迫,“所有人都说我会变成和我爸一样的混混,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没有。”
 5月19日,谢仁慈在图书馆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
5月19日,谢仁慈在图书馆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生如蚁,却美如神”
高三那年,谢仁慈每天早上七点到学校学英语,中午在桌子上趴着休息一会儿就起来看书,晚上十一点学校熄灯了才回家。
那时,她数学极差,每考完数学都要打电话给母亲大哭一场,母亲总说:“没关系,妈妈相信你。”
高考那年,她考了627分,一年提高了200多分,如愿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学。所有人都觉得谢仁慈是“高考黑马”,母亲心里清楚,“都是苦出来的”。
考完试的夏天,她一个人,从贵州出发,经过云南,进入西藏,一路上,住青旅,搭顺风车,见了很多人,渐渐打开自己。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贴吧里,这个压抑多年的女孩尝试晒出了自己的照片,写下一路上所见所感。
一次暴雨,谢仁慈和偶遇的旅友们一路上请求别人收留避雨,都被拒绝。
最后,一位守寺庙的老人收留了他们。这位老人没有鼻子,本该有鼻子的部位只剩下一个个狰狞的坑,他也没有嘴唇,说话时只有喉咙嗡嗡作响,并不清晰。
当时谢仁慈全身湿透,背包在滴水,老人拿出自己的衣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让她穿上,她想起生命可贵,“生如蚁,却美如神。”
进入大学后,谢仁慈自称“想得开大仙”。她开始结交朋友,又去了一次新疆和西藏,也认识了男朋友高琪蕰,对方也是残障人士,在麻省理工读本科。
高琪蕰失去右手后,曾在英国花高价做了仿生假肢,每次戴完假肢后会戴上手套,后来,他不想再忍受那些悄悄地“打量”,不再掩饰和遮挡,成为了右手上有一只金属钩子的“海盗船长”。
那段时间,谢仁慈逐渐变得自信和自知,她在日记中写下:长时间的自我觉醒与认同就像长跑一样,总气喘吁吁,总想放弃,还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呼吸、心率,这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自得其乐的挑战。
高琪蕰回国的前一天,谢仁慈在商场穿着假肢试裤子,左腿粗右腿细,售货员一直偷偷打量她,她忘不了,那种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目光。
那一瞬间,她炸了:藏来藏去还是被发现,这样掩藏有什么意思?回到酒店就把假肢外包装给撕了,只留下金属的躯干,裤子的右裤腿儿也剪了,“坦坦荡荡出门约会”。
站出来发声
撕掉假肢包装后,谢仁慈成了“阳光下的残障人士”。她享受到了残障人士应有的权利,不再担心特殊座位被一个玩手机的年轻人坐着,进残疾人卫生间也变得理直气壮。
她越来越愿意展露自己,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照片、文字。
回答完知乎问题的那个夜晚,谢仁慈一夜没睡,看着点赞数一点一点增加,把三千多条评论都看完了,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酷。
她承认,别人夸她酷,她会开心,这个爱抹口红的女孩从小就是“臭美精”。但这并非她的初衷,更多的,她希望别人能越过照片,看到残障群体的存在。
从前,谢仁慈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提高绩点、考托福、出国读书,实现小时候“上哈佛”的梦想,现在变成“站出来,第一步是先让别人知道这个群体,再去想权利的争取”。
这种“站出来”源于责任感,她反复强调,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利益既得者”——安静地享受多年学习的劳动成果,在这所知名政法大学读博,或者毕业后去当律师,拥有一个世俗定义下体面的未来。
只是一想到小时候,母亲为了让自己上一所普通学校,到处奔波,她便为其他残障人士心酸,“我一个少了一条腿的孩子,上普通学校都那么难,那些没双腿的、眼睛看不见的孩子,要怎么办?”
谈及未来,谢仁慈眼里有光,她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做成宣传册,给小朋友看,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残疾人小朋友和自己一样,都是很可爱的,不要把他们划分成“别人”,要把“他们”看成“我们”。
至于,纪录片找谁拍?资金从哪里来?这些东西她都在慢慢落实,她也迷茫,担心自己的能力,“但有一腔热血,总比没有要好”。
五月,一个将雨未雨的下午,谢仁慈在健身房锻炼。
她戴着高琪蕰亲手为她做的假肢,在动感单车上飞驰,一边听音乐,一边甩动头发,骑得比旁边的人还快。
忽然,她大笑了出来——假肢掉了。
谢仁慈动作熟练,右手捞起假肢,戴上,踩实,一边说“没事”,转眼又跨上了单车。(采写/记者 罗芊 重庆报道 摄影/记者 彭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