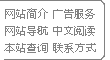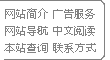寻找罗布人失去的世界
 100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涉险进入罗布荒原,
曾意外地发现过一个繁盛的渔村,那就是罗布人最早的家
园——阿不旦。100年后,这里只有黄沙漫漫,阿不旦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样从历史的沧桑中寻觅失落的文明?
如何破译罗布人在自然界变迁中历尽坎坷的抗争史?
于是,探寻罗布荒原上的文明,成为我矢志不渝的梦想。
杳无人烟的罗布荒原,是大自然留给后人的一个难解之谜,
荒原上罗布人的一切又是其中的谜中之谜。
多年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名著《亚洲腹地旅行
记》,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神秘古城丹丹乌里克,特别
是罗布荒原上的“探险家的驿站”阿不旦渔村,成为我梦
境中从不改变的终点,而重新找到并探访罗布人的“伊甸
园”—— 阿不旦,就是我一次次在塔里木旅行的目标之
一!
1984年,我在新疆做第一次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
旅行。8月中旬,来到若羌县的米兰镇。本来,我只是想
看看著名的米兰古城(即《汉书》记载过的伊循)和发现
过“带翼天使”壁画的米兰大寺。
在米兰镇,我无意中获悉,附近就居住着一批罗布人。
这时我突然发觉,阿不旦村已经近在眼前。
斯文赫定于1896年、1899~1901年几次来到亚洲腹地
的罗布荒原,都得到了罗布人的全力帮助。1896年,赫定
受到这支避处罗布泊岸边家园的罗布人的首领、清廷册封
的世袭五品伯克(伯克:是清代新疆塔里木地区地方长官,
一般均由当地人出任)昆其康的接待。而近代首次向外界
报道昆其康伯克其人和他的“封邑”阿不旦情况的,就是
那个颇多成就,也颇受非议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在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地理学的大事——“罗布泊位置之
争”中,昆其康伯克、阿不旦村,都成了“关键词”。
1921年后,因罗布泊北移,阿不旦为荒沙湮没无法居
住,这支罗布人便迁居于米兰镇。而渔村阿不旦之所以重
要,不仅因为它历来就是罗布泊一带的行政中心,也因为
一个多世纪以来探险家要在罗布荒原进出,就必须以阿不
旦为依托,只有在这儿,你才找得到合格的向导、驼夫,
才雇得到驼马,才能够补充给养。然而在我看来,实际上
它就是中国西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典型样本。
我没有想到,从1921年到1984年,60年过去了,我仍
能与阿不旦的罗布人相逢在米兰镇,这使我抵达阿不旦考
察的宿愿有了实现的可能。
是好客的孩子们把我们引到了罗布老人库万的家。
在库万·库都鲁克家度过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
库万老人清癯枯瘦,他的双眼藏匿在深隐的眼窝中,但在
回忆起几十年前在渔村阿不旦生活的往事时,眼睛却不时
放射出熠熠的光芒。和他交谈,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时间
隧道”,在往事中遨游。
库万的记忆是与世纪初的渔猎生涯分不开的。当天晚
上,他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将带领我返回如今已沦为沙漠
的阿不旦村,凭吊逝去的美好时日。
当我站在阿不旦村村头时,真是激情难抑。
这是一片长二三百米、宽三四十米的濒河(阿不旦河)
废墟,已经被弃置了一个花甲的岁月。她曾是罗布人幼年
的摇篮,童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她依
傍的河湖水域曾蕴藏着数不清的谜,曾酝酿了温馨缱绻的
往事。历史只是偶感风寒,打了一个喷嚏,罗布泊就化作
了天上的虹霓,飘散得无影无踪。在阿不旦生活了几个世
纪的罗布人不懂——也没有人能对他们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沧海桑田的水陆变化怎么就会强加在他们的头上。
库万告诉我,在阿不旦时,祖先讲的话能传到三天路
程之外的地方。这是说,在阿不旦兴盛时期罗布人的天地
相当宽广,但这也许是在比喻罗布人的祖先影响之大。
库万一一为我引见了村落的每一处遗址:乡约(伯克)
的官衙、库万自己的家、毛拉家的羊圈、渔人独木舟停靠
的码头,这里还有红柳做的针、罗布麻织的渔网……
望着这为流沙湮没的“庞培”,我好像走进了梦境。
时序在倒流,岁月在向起点狂奔,景物在替换,感觉在苏
醒,一支探险队即将走上村旁的古道,而我和库万就站在
路边,等待迟到的探险家。我们一同在为河水日益干涸、
植被成片死去、风沙每日肆虐而忧心忡忡。
1984年夏末,我在米兰见到的罗布人(特指世纪初曾
生活在阿不旦村的罗布人)除了库万,还有热合曼·阿布
拉、塔依尔、艾买提。据说那时在米兰镇,当年阿不旦的
村民仅有10人左右。塔依尔是罗布人中的长者,艾买提则
是昆其康伯克的直系后裔。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库万
,就是热合曼老人。
热合曼是“世纪同龄人”,他思路敏捷,记忆清晰。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罗布人一个世纪间在环境恶化的重
负下退出罗布荒原的有力见证,是将最后的罗布人离开阿
不旦前后的经历记录在史册上的人。
1984年8月,我在米兰镇只住了三天,但这短短的三
天,却改变了我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看法,最终使我将
自己的视野集中到人类与环境这个宏大的课题上来。而这
一切都萌生于阿不旦村的村头!
世世代代死守罗布泊水域,过着远离尘世、桃花园般
生活的罗布人,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
迁离家园,最终退出罗布荒原。
从1984年开始,我就像个寻找地平线上绿洲的“游方
僧”一样,在塔里木的古老村落和穷乡僻壤云游。1986年
、1992年 ,我都来过米兰镇,并看望了罗布老人库万与
热合曼。在这期间,我对罗布人和阿不旦的了解越来越多。
1876年11月,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乘船沿塔里
木河下游紊乱的河道前往罗布泊。他的船队路经了一个个
从不为外人所知的罗布渔村,它们都归驻在阿不旦的伯克
昆其康统辖。普氏在探险记和书信中,记下了对阿不旦的
观感:阿不旦是个固守旧俗的避世桃源。这里的罗布人不
知道目前谁主宰着新疆,也不关心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事情
。他们世世代代死守罗布泊水域,过着寂寞但心安理得的
日子。由于极度的闭塞,而且与塔里木社会完全脱节,使
阿不旦成为罗布荒原一个远古时期的“活化石”。阿不旦
人的生活用品都取自身边。这里芦苇有8米高,直径四五
公分,他们就用芦苇盖房、取暖、架桥、铺路,芦花可以
充填衣被,可以熬成浓浆代替食糖,他们的衣着是由当地
的野麻(后来就被称为“罗布麻”)织成,主食有吃不完
的鱼,再加上水禽。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不旦,这就是罗
布人的美好世界。!
20年后的1896年,斯文赫定也乘独木舟抵达了罗布人
的“首府”阿不旦。《穿越亚洲》一书有关阿不旦的记载
,是全书最有趣的部分。当独木舟靠拢在阿不旦的码头时
,凭普尔热瓦尔斯基书中的一幅插图,赫定在人群中一眼
就认出了“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当时昆其康已
经86岁,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告诉赫定,如今的阿
不旦是他的祖父于公元1720年建立的。赫定当时也非常详
细地记录了阿不旦的生活情况。罗布人每家有一个或几个
“恰普干”,所谓恰普干,就是专门为了捕鱼而由人工修
整的水道。每家的恰普干就是罗布人事实上的“私人领地
”。据赫定观察,阿不旦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世居罗布泊
畔的罗布人只有在远离尘世的阿不旦,才能无视世事的变
迁,恪守着祖先的旧俗过着贫穷而安乐的生活。这当然与
昆其康本人就住在阿不旦有关。但奇怪的是,以赫定这样
敏锐、勤奋的观察家,竟未能见微知著,没有注意到阿不
旦村已经处在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一种恶性循环,已经
使阿不旦濒于环境崩溃的临界点。换句话说,这个表面繁
荣兴盛的首府,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
1900年春天,赫定再次抵达罗布荒原。在从北向南的
探险考察时,他抵达了罗布泊从未为人所知的北岸。这时
他才得知,昆其康伯克于1898年去世,他一死,阿不旦立
即就失去了权威的罗布人废弃了。向最终退出罗布荒原迈
出第一步的罗布人,将首府迁至西南一天路程之外的玉尔
特恰普干。
在罗布方言里,阿不旦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
之意。罗布人总是将自己的首府叫“阿不旦”。这样,昆
其康伯克的阿不旦,就成了“老阿不旦”或“真正的阿不
旦”,玉尔特恰普干沿袭了阿不旦的名字,便是新阿不旦
。奇怪的是,罗布人首府的新旧变迁,竟长期不为人所知
。1996年以前,我也以为自己1984年到过的阿不旦,就是
昆其康伯克的老阿不旦。但事实上从1896年以后,长达一
个世纪以来,外人从来也没有到过罗布泊故岸边的老阿不
旦。1900年的赫定、1907年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9年
的日本释子橘瑞超,直到1981年的中国科学院罗布泊综合
科学考察队、1984年的我自己,所去过的阿不旦,其实都
不是老阿不旦而是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
弄明白阿不旦的变迁后,真使我沮丧,但又激发了我
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促成了我1997年、1998年两次寻找
老阿不旦的探险考察。
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盛极
一时的绿色王国。而现在罗布老人记忆中的罗布方舟早已
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漫漫荒漠。
1997年8月,在来米兰前,我就获悉库万已经在当年
的7月去世于若羌县县城。罗布老人热合曼热情地接待了
我。这次就罗布人和阿不旦的历史,我获得了许多前所未
闻的重要情况 。这些情况我已经在我的新著《最后的罗
布人》之中作了详细的介绍。但遗憾的是,我们寻找老阿
不旦的探险却失败了。
1998年10月,我再次来到了罗布荒原,探寻其间的未
知世界。
1998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无法生存而不得不放弃老阿
不旦的100周年,也是罗布人迁居最后的聚居地新阿不旦
100周年。然而时隔一个世纪,将由谁来亲手结系起新老
阿不旦突然中断的历史呢?谁将是老阿不旦放弃百年后的
第一个来访者?
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1998年10月10日我再次抵达米
兰镇开始了又一轮考察。
1998年10月11日清晨,热合曼领我们踏上前往老阿不
旦荒疏已久的路。这次我们带有“奔驰”沙漠车和先进的
GPS(卫星定位仪),并掌握了前人测定的老阿不旦的经纬
度。但我真正依靠的只是罗布人对故园刻骨铭心的记忆和
与生俱来的方向感。斯文赫定曾说,即便蒙上双眼,罗布
人也可以凭直觉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方向,在全无参照物的
荒野上认路,是他们生存的本能。
沙漠车磕磕绊绊行走在沙包、碱滩之间。荒野一望无
际,死寂难言给人无限的压抑。我们事实上是沿着罗布人
退出罗布沙漠的路线,反向一直向老阿不旦前进。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罗布人居住遗址叫奥特开提干乌依,
它的含义就是“火烧了房子的地方”。1898年因地下水位
上升、湖泊逐渐成为沼泽等因素而撤离老阿不旦的罗布人
先定居在此,一次为驱赶蚊蝇点燃芦苇,控制不住的火势
将整个村子烧光,他们才搬到新阿不旦。而这个地名就成
了罗布人退出沙漠的“里程碑”。
再踏上路途,环境恶劣多了。当热合曼老人告诉我们,
他只是在60年前到过老阿不旦时,大家不禁对他能否领我
们抵达目的地持怀疑态度。热合曼仍然不紧不慢地指着路
,而前方的沙包却越来越密集。同行者建议:“杨老师,
还是依靠GPS吧。向西3公里,再折向正北2公里,就是老
阿不旦了。”话刚说完,热合曼沉稳地说:“诺,这就是
老阿不旦村了!”
如果不是热合曼提醒,我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就是那个
繁盛了一两百年的阿不旦村!原来那一个个密集的沙包就
是压在孙悟空背上的五行山,在每个沙包之下,都是罗布
人的家。而我以为是一段为流沙阻塞的河道的深坑,其实
就是阿不旦村中心的“广场”,那个深坑是百年来风的“
杰作”。地面残存的芦苇厚达几十公分,而瓷实的芦苇根
几乎插不进一根筷子。据赫定记载,老阿不旦是罗布泊岸
边唯一的一块干燥的高岗,而目前它已经快要发展成一个
硕大无比的沙山。那一望无际的罗布泊水域在哪儿呢?那
浓密无隙的芦苇、遮天蔽日的植被又生长在何方?是谁施
加了法术使那一人长的大头鱼、那出没在密林灌丛中的马
鹿、那携家带口的水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冥冥中的
什么力量驱使那终日在村头享受秋阳的老人、孩子,那编
织罗布麻的妇女,那与世无争的勤劳的罗布人,都弃家园
于不顾,而流落他方?
刮了一天的风停了。随之而来的是失聪般的寂静。我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找到并抵达了老阿不旦,但我却
为之背上了难以息肩的精神重负!
在老阿不旦的村头,我与热合曼老人并肩漫步。老人
沉默无语,但他的表情已深深感染了我。
作为100年来老阿不旦村第一个外来人、探访者,是
历史的机运赋予了我重访阿不旦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已经成为赫定的后继人,成了昆其康伯克期待已久的贵
宾!
返程分外沉闷漫长。我们在热合曼的带领下,依罗布
人“败北”的路线,探访了夏卡勒、库姆恰普干、吐逊恰
普干、新阿不旦等罗布人“遗留”在荒沙中的村落,当然
,如今它们早已沦没为无人的沙海。
路上,我想起库万对我讲过的罗布人的传说:在烟波
浩淼的罗布泊中,有许多一人长的“鱼王”,每逢春风吹
遍荒野,它们就跃上岸边,在沙滩打个滚,摇身一变,成
为壮硕的马鹿,跑进浓密的胡杨林。而每逢秋风摇落了树
叶,胡杨褪尽夏天华丽的衣衫,马鹿又跑到罗布泊岸边,
在沙窝一滚,还原成大鱼,再游到湖泊的深处。
就在返回米兰绿洲的路上,我突然品味出这个传说深
刻的意蕴。其实这只是罗布人对罗布荒原环境日益恶化的
一个心理折射。在不知不觉间,本是浩瀚无边的罗布泊已
经日见干涸,在其中悠游的大鱼难以存身,连活动都活动
不开了。在罗布人想像中,鱼只能以鹿的形体,转至胡杨
林中藏身。但如果胡杨和植被也处在了不可遏止的衰颓过
程,那么罗布荒原就不再有生物的寄身之地!这是多么浪
漫又多么凄 伤的幻觉啊!这是多么紧迫而又多么漫长的
过程!一旦罗布人已经认识到水陆都不适宜人居住时,那
么除了放弃先民的发轫之地,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绿洲是中国西部居民的方舟,是人的栖息地。阿不旦
成了罗布泊的“弃婴”,罗布沙漠被划为人类的禁区。而
罗布沙漠中一个个原来繁荣的村镇,都成了沉没的方舟。
如果整个塔里木有朝一日也变作巨大的“泰坦尼克号”,
到那时再弃船逃生,是不是已经太迟太迟了呢?
前方是米兰一抹绿色的林带,身后是沉没百年的罗布
人的方舟,它们之间的路程只有10个小时,但我却恍如跨
越了几十个世纪漫长而坎坷的岁月!
我回首向阿不旦告别时,看到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新
的绿洲。那是因为我梦想成疾而致使时空错位,还是罗布
人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此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当人类重
返阿不旦居住时,能够置身于先行者的行列……
100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涉险进入罗布荒原,
曾意外地发现过一个繁盛的渔村,那就是罗布人最早的家
园——阿不旦。100年后,这里只有黄沙漫漫,阿不旦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样从历史的沧桑中寻觅失落的文明?
如何破译罗布人在自然界变迁中历尽坎坷的抗争史?
于是,探寻罗布荒原上的文明,成为我矢志不渝的梦想。
杳无人烟的罗布荒原,是大自然留给后人的一个难解之谜,
荒原上罗布人的一切又是其中的谜中之谜。
多年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名著《亚洲腹地旅行
记》,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神秘古城丹丹乌里克,特别
是罗布荒原上的“探险家的驿站”阿不旦渔村,成为我梦
境中从不改变的终点,而重新找到并探访罗布人的“伊甸
园”—— 阿不旦,就是我一次次在塔里木旅行的目标之
一!
1984年,我在新疆做第一次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
旅行。8月中旬,来到若羌县的米兰镇。本来,我只是想
看看著名的米兰古城(即《汉书》记载过的伊循)和发现
过“带翼天使”壁画的米兰大寺。
在米兰镇,我无意中获悉,附近就居住着一批罗布人。
这时我突然发觉,阿不旦村已经近在眼前。
斯文赫定于1896年、1899~1901年几次来到亚洲腹地
的罗布荒原,都得到了罗布人的全力帮助。1896年,赫定
受到这支避处罗布泊岸边家园的罗布人的首领、清廷册封
的世袭五品伯克(伯克:是清代新疆塔里木地区地方长官,
一般均由当地人出任)昆其康的接待。而近代首次向外界
报道昆其康伯克其人和他的“封邑”阿不旦情况的,就是
那个颇多成就,也颇受非议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在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地理学的大事——“罗布泊位置之
争”中,昆其康伯克、阿不旦村,都成了“关键词”。
1921年后,因罗布泊北移,阿不旦为荒沙湮没无法居
住,这支罗布人便迁居于米兰镇。而渔村阿不旦之所以重
要,不仅因为它历来就是罗布泊一带的行政中心,也因为
一个多世纪以来探险家要在罗布荒原进出,就必须以阿不
旦为依托,只有在这儿,你才找得到合格的向导、驼夫,
才雇得到驼马,才能够补充给养。然而在我看来,实际上
它就是中国西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典型样本。
我没有想到,从1921年到1984年,60年过去了,我仍
能与阿不旦的罗布人相逢在米兰镇,这使我抵达阿不旦考
察的宿愿有了实现的可能。
是好客的孩子们把我们引到了罗布老人库万的家。
在库万·库都鲁克家度过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
库万老人清癯枯瘦,他的双眼藏匿在深隐的眼窝中,但在
回忆起几十年前在渔村阿不旦生活的往事时,眼睛却不时
放射出熠熠的光芒。和他交谈,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时间
隧道”,在往事中遨游。
库万的记忆是与世纪初的渔猎生涯分不开的。当天晚
上,他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将带领我返回如今已沦为沙漠
的阿不旦村,凭吊逝去的美好时日。
当我站在阿不旦村村头时,真是激情难抑。
这是一片长二三百米、宽三四十米的濒河(阿不旦河)
废墟,已经被弃置了一个花甲的岁月。她曾是罗布人幼年
的摇篮,童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她依
傍的河湖水域曾蕴藏着数不清的谜,曾酝酿了温馨缱绻的
往事。历史只是偶感风寒,打了一个喷嚏,罗布泊就化作
了天上的虹霓,飘散得无影无踪。在阿不旦生活了几个世
纪的罗布人不懂——也没有人能对他们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沧海桑田的水陆变化怎么就会强加在他们的头上。
库万告诉我,在阿不旦时,祖先讲的话能传到三天路
程之外的地方。这是说,在阿不旦兴盛时期罗布人的天地
相当宽广,但这也许是在比喻罗布人的祖先影响之大。
库万一一为我引见了村落的每一处遗址:乡约(伯克)
的官衙、库万自己的家、毛拉家的羊圈、渔人独木舟停靠
的码头,这里还有红柳做的针、罗布麻织的渔网……
望着这为流沙湮没的“庞培”,我好像走进了梦境。
时序在倒流,岁月在向起点狂奔,景物在替换,感觉在苏
醒,一支探险队即将走上村旁的古道,而我和库万就站在
路边,等待迟到的探险家。我们一同在为河水日益干涸、
植被成片死去、风沙每日肆虐而忧心忡忡。
1984年夏末,我在米兰见到的罗布人(特指世纪初曾
生活在阿不旦村的罗布人)除了库万,还有热合曼·阿布
拉、塔依尔、艾买提。据说那时在米兰镇,当年阿不旦的
村民仅有10人左右。塔依尔是罗布人中的长者,艾买提则
是昆其康伯克的直系后裔。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库万
,就是热合曼老人。
热合曼是“世纪同龄人”,他思路敏捷,记忆清晰。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罗布人一个世纪间在环境恶化的重
负下退出罗布荒原的有力见证,是将最后的罗布人离开阿
不旦前后的经历记录在史册上的人。
1984年8月,我在米兰镇只住了三天,但这短短的三
天,却改变了我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看法,最终使我将
自己的视野集中到人类与环境这个宏大的课题上来。而这
一切都萌生于阿不旦村的村头!
世世代代死守罗布泊水域,过着远离尘世、桃花园般
生活的罗布人,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
迁离家园,最终退出罗布荒原。
从1984年开始,我就像个寻找地平线上绿洲的“游方
僧”一样,在塔里木的古老村落和穷乡僻壤云游。1986年
、1992年 ,我都来过米兰镇,并看望了罗布老人库万与
热合曼。在这期间,我对罗布人和阿不旦的了解越来越多。
1876年11月,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乘船沿塔里
木河下游紊乱的河道前往罗布泊。他的船队路经了一个个
从不为外人所知的罗布渔村,它们都归驻在阿不旦的伯克
昆其康统辖。普氏在探险记和书信中,记下了对阿不旦的
观感:阿不旦是个固守旧俗的避世桃源。这里的罗布人不
知道目前谁主宰着新疆,也不关心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事情
。他们世世代代死守罗布泊水域,过着寂寞但心安理得的
日子。由于极度的闭塞,而且与塔里木社会完全脱节,使
阿不旦成为罗布荒原一个远古时期的“活化石”。阿不旦
人的生活用品都取自身边。这里芦苇有8米高,直径四五
公分,他们就用芦苇盖房、取暖、架桥、铺路,芦花可以
充填衣被,可以熬成浓浆代替食糖,他们的衣着是由当地
的野麻(后来就被称为“罗布麻”)织成,主食有吃不完
的鱼,再加上水禽。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不旦,这就是罗
布人的美好世界。!
20年后的1896年,斯文赫定也乘独木舟抵达了罗布人
的“首府”阿不旦。《穿越亚洲》一书有关阿不旦的记载
,是全书最有趣的部分。当独木舟靠拢在阿不旦的码头时
,凭普尔热瓦尔斯基书中的一幅插图,赫定在人群中一眼
就认出了“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当时昆其康已
经86岁,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告诉赫定,如今的阿
不旦是他的祖父于公元1720年建立的。赫定当时也非常详
细地记录了阿不旦的生活情况。罗布人每家有一个或几个
“恰普干”,所谓恰普干,就是专门为了捕鱼而由人工修
整的水道。每家的恰普干就是罗布人事实上的“私人领地
”。据赫定观察,阿不旦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世居罗布泊
畔的罗布人只有在远离尘世的阿不旦,才能无视世事的变
迁,恪守着祖先的旧俗过着贫穷而安乐的生活。这当然与
昆其康本人就住在阿不旦有关。但奇怪的是,以赫定这样
敏锐、勤奋的观察家,竟未能见微知著,没有注意到阿不
旦村已经处在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一种恶性循环,已经
使阿不旦濒于环境崩溃的临界点。换句话说,这个表面繁
荣兴盛的首府,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
1900年春天,赫定再次抵达罗布荒原。在从北向南的
探险考察时,他抵达了罗布泊从未为人所知的北岸。这时
他才得知,昆其康伯克于1898年去世,他一死,阿不旦立
即就失去了权威的罗布人废弃了。向最终退出罗布荒原迈
出第一步的罗布人,将首府迁至西南一天路程之外的玉尔
特恰普干。
在罗布方言里,阿不旦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
之意。罗布人总是将自己的首府叫“阿不旦”。这样,昆
其康伯克的阿不旦,就成了“老阿不旦”或“真正的阿不
旦”,玉尔特恰普干沿袭了阿不旦的名字,便是新阿不旦
。奇怪的是,罗布人首府的新旧变迁,竟长期不为人所知
。1996年以前,我也以为自己1984年到过的阿不旦,就是
昆其康伯克的老阿不旦。但事实上从1896年以后,长达一
个世纪以来,外人从来也没有到过罗布泊故岸边的老阿不
旦。1900年的赫定、1907年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9年
的日本释子橘瑞超,直到1981年的中国科学院罗布泊综合
科学考察队、1984年的我自己,所去过的阿不旦,其实都
不是老阿不旦而是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
弄明白阿不旦的变迁后,真使我沮丧,但又激发了我
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促成了我1997年、1998年两次寻找
老阿不旦的探险考察。
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盛极
一时的绿色王国。而现在罗布老人记忆中的罗布方舟早已
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漫漫荒漠。
1997年8月,在来米兰前,我就获悉库万已经在当年
的7月去世于若羌县县城。罗布老人热合曼热情地接待了
我。这次就罗布人和阿不旦的历史,我获得了许多前所未
闻的重要情况 。这些情况我已经在我的新著《最后的罗
布人》之中作了详细的介绍。但遗憾的是,我们寻找老阿
不旦的探险却失败了。
1998年10月,我再次来到了罗布荒原,探寻其间的未
知世界。
1998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无法生存而不得不放弃老阿
不旦的100周年,也是罗布人迁居最后的聚居地新阿不旦
100周年。然而时隔一个世纪,将由谁来亲手结系起新老
阿不旦突然中断的历史呢?谁将是老阿不旦放弃百年后的
第一个来访者?
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1998年10月10日我再次抵达米
兰镇开始了又一轮考察。
1998年10月11日清晨,热合曼领我们踏上前往老阿不
旦荒疏已久的路。这次我们带有“奔驰”沙漠车和先进的
GPS(卫星定位仪),并掌握了前人测定的老阿不旦的经纬
度。但我真正依靠的只是罗布人对故园刻骨铭心的记忆和
与生俱来的方向感。斯文赫定曾说,即便蒙上双眼,罗布
人也可以凭直觉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方向,在全无参照物的
荒野上认路,是他们生存的本能。
沙漠车磕磕绊绊行走在沙包、碱滩之间。荒野一望无
际,死寂难言给人无限的压抑。我们事实上是沿着罗布人
退出罗布沙漠的路线,反向一直向老阿不旦前进。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罗布人居住遗址叫奥特开提干乌依,
它的含义就是“火烧了房子的地方”。1898年因地下水位
上升、湖泊逐渐成为沼泽等因素而撤离老阿不旦的罗布人
先定居在此,一次为驱赶蚊蝇点燃芦苇,控制不住的火势
将整个村子烧光,他们才搬到新阿不旦。而这个地名就成
了罗布人退出沙漠的“里程碑”。
再踏上路途,环境恶劣多了。当热合曼老人告诉我们,
他只是在60年前到过老阿不旦时,大家不禁对他能否领我
们抵达目的地持怀疑态度。热合曼仍然不紧不慢地指着路
,而前方的沙包却越来越密集。同行者建议:“杨老师,
还是依靠GPS吧。向西3公里,再折向正北2公里,就是老
阿不旦了。”话刚说完,热合曼沉稳地说:“诺,这就是
老阿不旦村了!”
如果不是热合曼提醒,我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就是那个
繁盛了一两百年的阿不旦村!原来那一个个密集的沙包就
是压在孙悟空背上的五行山,在每个沙包之下,都是罗布
人的家。而我以为是一段为流沙阻塞的河道的深坑,其实
就是阿不旦村中心的“广场”,那个深坑是百年来风的“
杰作”。地面残存的芦苇厚达几十公分,而瓷实的芦苇根
几乎插不进一根筷子。据赫定记载,老阿不旦是罗布泊岸
边唯一的一块干燥的高岗,而目前它已经快要发展成一个
硕大无比的沙山。那一望无际的罗布泊水域在哪儿呢?那
浓密无隙的芦苇、遮天蔽日的植被又生长在何方?是谁施
加了法术使那一人长的大头鱼、那出没在密林灌丛中的马
鹿、那携家带口的水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冥冥中的
什么力量驱使那终日在村头享受秋阳的老人、孩子,那编
织罗布麻的妇女,那与世无争的勤劳的罗布人,都弃家园
于不顾,而流落他方?
刮了一天的风停了。随之而来的是失聪般的寂静。我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找到并抵达了老阿不旦,但我却
为之背上了难以息肩的精神重负!
在老阿不旦的村头,我与热合曼老人并肩漫步。老人
沉默无语,但他的表情已深深感染了我。
作为100年来老阿不旦村第一个外来人、探访者,是
历史的机运赋予了我重访阿不旦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已经成为赫定的后继人,成了昆其康伯克期待已久的贵
宾!
返程分外沉闷漫长。我们在热合曼的带领下,依罗布
人“败北”的路线,探访了夏卡勒、库姆恰普干、吐逊恰
普干、新阿不旦等罗布人“遗留”在荒沙中的村落,当然
,如今它们早已沦没为无人的沙海。
路上,我想起库万对我讲过的罗布人的传说:在烟波
浩淼的罗布泊中,有许多一人长的“鱼王”,每逢春风吹
遍荒野,它们就跃上岸边,在沙滩打个滚,摇身一变,成
为壮硕的马鹿,跑进浓密的胡杨林。而每逢秋风摇落了树
叶,胡杨褪尽夏天华丽的衣衫,马鹿又跑到罗布泊岸边,
在沙窝一滚,还原成大鱼,再游到湖泊的深处。
就在返回米兰绿洲的路上,我突然品味出这个传说深
刻的意蕴。其实这只是罗布人对罗布荒原环境日益恶化的
一个心理折射。在不知不觉间,本是浩瀚无边的罗布泊已
经日见干涸,在其中悠游的大鱼难以存身,连活动都活动
不开了。在罗布人想像中,鱼只能以鹿的形体,转至胡杨
林中藏身。但如果胡杨和植被也处在了不可遏止的衰颓过
程,那么罗布荒原就不再有生物的寄身之地!这是多么浪
漫又多么凄 伤的幻觉啊!这是多么紧迫而又多么漫长的
过程!一旦罗布人已经认识到水陆都不适宜人居住时,那
么除了放弃先民的发轫之地,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绿洲是中国西部居民的方舟,是人的栖息地。阿不旦
成了罗布泊的“弃婴”,罗布沙漠被划为人类的禁区。而
罗布沙漠中一个个原来繁荣的村镇,都成了沉没的方舟。
如果整个塔里木有朝一日也变作巨大的“泰坦尼克号”,
到那时再弃船逃生,是不是已经太迟太迟了呢?
前方是米兰一抹绿色的林带,身后是沉没百年的罗布
人的方舟,它们之间的路程只有10个小时,但我却恍如跨
越了几十个世纪漫长而坎坷的岁月!
我回首向阿不旦告别时,看到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新
的绿洲。那是因为我梦想成疾而致使时空错位,还是罗布
人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此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当人类重
返阿不旦居住时,能够置身于先行者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