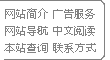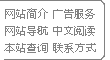挑战“母亲河”
——记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漂流探险队
文●达兰
中国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的青藏高原,被世人称为南
、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极”。而全长6300公里、落差5
400米的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其正源沱沱河就是源
自这里的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海拔6621米)冰川脚下。
1998年8月,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漂流探险队从成
都出发,开始了一次世纪末的江源之旅。
走过无人区
沱沱河源区共约三千多平方公里。我们乘车近十天抵
达距无人区最近的多玛区政府所在地雁石坪后,于8月31
日,在区长的安排下分乘两辆卡车、一辆吉普进入无人区。
然而车行不久便相继“趴窝”了——向导那琼告诉我
们,这个季节通往源头姜古迪如冰川的路全是湿地、沼泽,
汽车根本无法通过。无奈,在冬季乘车只需一两天的二百
多公里路程,我们只好步行了。当那琼连嚷带比划地说出:
“十天”这两个字眼时,大家是真正的“目瞪口呆”了。
这一天,我们首次露宿无人区,等待向导们把30多头
牦牛赶来,驮运装备。
为了适应新的探险生活方式,十一位女队员必须从搭
帐蓬、吹气垫床、使用睡袋和做饭开始。幸好队伍中还有
六位高原探险经验丰富的男士做后勤,不过,大家都明白,
在这个走几步就气喘如牛、头痛欲裂的“屋脊地带”,每
个人都必须“先依靠自己,再帮助别人”。
晚上8点多,刚端起盛着米饭、萝卜炖羊肉的军用饭
盒,来自江苏的23岁的姑娘季红悄悄对我说:“不想影响
大家,我还是决定回去了。”她早在雁石坪就因缺氧被急
救过一次,后来咬着牙跟到这里,现在流着泪挥别了队伍,
搭拖车返回了。
星夜朗朗,夜半却听见冰雹敲击帐蓬的声音。我们已
经穿上了几乎所有的衣服,但寒冷还是使得许多女队员将
军用水壶盛上开水放在睡袋里取暖,才勉强入睡。
9月2日上午,积雪刚刚融化,天边云雾散尽,营地正
前方的地平线上,现出冰雪金字塔般的格拉丹东主峰,在
阳光下成为苍茫草原上唯一的亮点。
向导那琼、欧要等人把我们的行李、装备全部捆到牦
牛背上,该出发了。
习惯了走柏油路、过人行道的我们,怀着新奇,渴望
而又不安的心情,踏上面前一望无际的沼泽草甸,向着远
方的格拉丹东进发。
这一走,就是十天。
高原的气候变化多端,为了防止被烈日灼伤,大家不
得不戴上帽子、墨镜、手套,已顾不上美观的女孩子们用
围巾、口罩把头脸蒙个严实;与此同时,迷彩花纹的雨衣
、雨裤也要穿在身上,以防冰雹风雪随时降临——这副样
子,大家互相戏称为“绿毛龟”。
海拔越来越高,从3000米到5000米。在这个连呼吸都
困难的地方,我们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走十几二十公里,
翻山、过河、或在沼泽草甸上跳跃前进。这时才真正理解
了行前一位探险者说的话:“那个时候你会恨不得把耳朵
都揪下来扔掉!”
于是,每天宿营时分,烧着牛粪炉子的帐篷就成了温
暖的家,萝卜、土豆炖羊肉也如同美味佳肴。
我总也忘不了有一天夜晚,我被牛粪烟呛得跑出帐篷,
抬头之际,只见夜幕低垂,寒星点点,月亮正穿云而过,
天地浑然一体。“好像走着走着,就能走到天堂里去了!
”队里年龄最小的“幺妹”鲜红突在冲过来,说完这句话
又傻笑着跑开不知去哪儿了。她脸上的表情瞬间成为我记
忆中一个永远的定格。
9月4日这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日记里
留下了这样的话:“从没想过,‘9月4日’与‘九死一生’
谐音!”
这一天的日出奇美,把离我们不远的格拉丹东染上一
种温暖而奇特的红色。早起的“摄影爱好者”们一声不吭,
疯子般地抬着三角架四处乱跑,抓取转瞬即逝的美景。
出发后,刚刚行至中午,汪永晨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
地,陆续赶来的队友们七手八脚地扶她躺在怀里,捏人中,
搓手、搓脚——氧气瓶被走在前面的向导拿着,三位后勤
队员立刻不顾性命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奔跑着追赶而去。
悠悠醒转的汪永晨虚弱地告诉大家:“右半身全麻了。”
继而泪流满面。终于向导欧要携了氧气瓶快马赶来,才算
转危为安。事后才知道三个后勤男同胞几乎跑死,本来体
壮如牛的司机梁师傅自此元气大伤,成了病号。
走了这几日,常常有人哭。幺妹在江梗曲头疼得哭;
71岁的“姥姥”刘沙几乎每天从“特批”给她的牦牛背上
摔下来,只哭了一次;摄影记者燕子发高烧,想家哭;歌
手刘浪走路累得瘫倒在地,却哭着说:“找到感觉了”;
被高原反应折磨到出现幻觉的熊梦玮哭喊着让大家“拿枪
打恶魔”;后勤队员刘健为救汪永晨急得跪地大哭……
对我来说,这些“哭”同他(她)们的“笑”一样珍贵。
1998年9月10日下午5点左右,中国女子长江源漂流探
险队经过9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距源头仅十多公里的
玛曲河口。
出发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沱沱河的主流河道——
这引诱着我们不辞辛苦,迢迢而至的江源之水!
奔腾着,喧嚣着的沱沱河,使我们连日来已疲惫之极
的身心又兴奋起来——几天后,我们将乘橡皮船经此顺流
而下。
风雪大江源
9月11日上午,背上干粮、相机,我们又出发了,这
将是最后一天步行。向导们说,我们将在傍晚时分抵达目
的地:姜古迪如冰川。
一路上,急促的喘息和越发沉重的双腿告诉我们,这
里的海拔绝不会低于5200米。天气多变,行至下午3点多,
只见远处姜古迪如方向的天空已是阴云密布。10天来的高
原经验使我们意识到:大家正向着一场来势凶猛的暴风雪
走去。
果然,姜古迪如似乎是要诚心考验一下我们这群“闯
入者”,雨滴很快变成雪粒,而后又凝结成冰雹向我们袭
来。这是此行遇到持续时间最长,最大的一场风雪。
步行10天,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当苍凉、冷峻的风雪
大江源,如一幅壮丽的黑白画卷展现在大家眼前时,连日
来始终坚持走在队伍前面的小熊再也坚持不住了,不得不
输氧抢救。互相搀扶着,一直走到冰川脚下几十米处安营
扎寨。
姜古迪如,长江之源,迎来了他历史上女人最多的一
天。请原谅我们暂时打破一下你那亘古的静寂罢。
姜古迪如,翻译成汉语,意为“野狼出没的冰石地带”。
营地旁边几十米高的冰山,不过是姜古迪如冰川的末端而
已。乌云笼罩的格拉丹东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这条庞大的,古老的,凝固的冰河是如何奔腾而下,又在
这儿嘎然而止。
冰川滴水融化成纵横交错的小溪,这就是长江正源沱
沱河的顶端。
此刻才真正明白,长江是有生命的,这时不正是她的
婴儿时代?古老的冰川凝固着生就她的那份古老浩瀚。
次日午后,雪霁天晴。全队在冰川脚下举行了立碑仪
式。事实上,铜制的碑早已被莽撞的牦牛踩坏,而向导们
亦劝告我们,在这儿想立一尊永久性的碑几乎是不可能的
——沉的运不上来,轻的又经不住风雪和石流的袭击,“
以前立的一两个碑都无影无踪了。”然而向导的话并没能
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因为此刻,碑已在心中。
这一天,也是《今日女报》记者熊梦玮25岁的生日,
嗲嗲的南方口音和少见的娇嫩皮肤引得大伙叫她“熊贵妃”,
然而江源一行,把这个家里最小的娇女儿也变得一天天坚
强起来。此刻,在温暖的帐篷里,在大家的亲吻和祝福里,
她似乎忘记了吸氧时的痛苦,把仅存的一点奶糖、话梅、
牛肉干全部拿出来请客,早有有心人为她的生日准备了生
日卡,每人一句祝福的留言。
喧闹声中,冰川寂然融化的滴答声恍然又在耳际絮语,
在5500米的世界屋脊上,这个生日如此奢侈!
漂过长江源
9月13日中午,在牦牛背上捆了十多天的橡皮船,终
于被“松绑”,抬到河边。我们将从这里放船,全程漂流
沱沱河300多公里的源头河段。这对大多从未有过漂流经
验的女队员们来说,将又是一段全新的探险历程。
和我们比起来,这几只橡皮船可算得上久经风雨了—
—在轰动全国的1986年“长漂”中,它们就曾为中国队效
力。给橡皮船打气是标准的“高原体力活”——全体上阵,
每人20下。之后是“细活”——全面检查船体,修补漏气
点,排除隐患。
为了适应水上漂流,女队员们穿上雨衣、雨裤,有的
还用皮筋扎紧袖口和裤脚;红色救生衣人手一件,另外还
要留好一套干衣服、一双鞋,塞进防水袋,以备打湿后替
换。
向导们已与我们道别,部分后勤队员也一同从陆路赶
赴几天后的上岸地点等候我们。这就样,八名女队员,四
位后勤男同胞及一位摄像记者一起,戴上粗线手套,握起
船桨,开始了艰难而浪漫的漂流之旅。
在江源无人区辽阔的网状水系上划行,有着与陆地上
完全不同的视角,水的动感令人遐想:如果说大地是人类
的母亲,我们应该是在母亲的血脉里行进。
然而,可以“遐想”的时候很少。划船、抢滩,最艰
难的是下到冰冷刺骨的水里,把触滩搁浅的船拖进深水。
高原的天说变就变,风雨来临,大家得在船上扯起雨布暂
避一时。
虽然高原上快十点天才黑,我们却不得不在下午五六
点钟就收船,上岸宿营。迟了往往会变天,风大得帐篷都
搭不起来,何况必须要有时间拾柴、拣牛粪烧饭、取暖、
烤湿衣服。第二天,又要收帐篷、装船,再次起航。
在大家常常回味的故事里,说得最多的就是“9·13
”。那是放船的第一天,也许是兴奋了些,我们直划到夜
幕降临,眼前伸手不见五指了。失去方向,在网状水系里
常常会走错河道,离目的地越来越远,夜的冷、水的凉、
肚子空,会要了人命。大家只得把橡皮船拉上河间滩地,
涉水上岸,步行寻找尚未走远的向导们的帐篷。
淌过十多条大大小小的水流,几个人全湿透了,寒冷
和疲惫使大家全身发抖,喘息声听来更像呻吟和哭泣。然
而不敢稍停,否则人会冻僵。只有在黑暗里不停地走、再
走……没有体验,不会明白一件事:世上最美的是黑暗路
途上的一占灯火。
当赶来的后勤队员不由分说一把抓过我的双手塞进自
己的衣服,贴到他那滚烫的皮肤上时,我觉得冻僵的脸像
冰川一样,一滴滴地融化了……
9月16日中午,下了一夜的雪仍没有停的迹象,我们
只得“扎雪班”了——在雪水里拖船搞不好要冻伤人。
下午3点多,一部分人去河边垂钓“寒江雪”,余下
我和刘浪、幺妹三个在帐篷里闲聊。突然一声凄厉的叫声
传来:“狼来了!”三人赶紧冲出帐外,只见“摄影发烧
友”胡静正全速向帐篷跑来,走近一看,脸色苍白,看来
不是装的,再定睛一看,不远处的山坡上,衬着苍天,有
五头或蹲或站的狼!说不准就是它们,昨晚在距我们帐篷
十米远的雪地上留下了那重重叠叠的“梅花”足迹。
胡静是在企图近距离拍摄野狼,却从镜头中突然发现
一头狼冲她直奔而来时,吓得疾跑回来的,而此时它们似
乎只打算静静地守望我们这群人。对峙片刻。刘浪招呼幺
妹,一个拿了铁锹,一个拎了菜刀,一步一回头走向远处
河边的其它队友,打算去报信。然而狼们却始终在山坡上
忽隐忽现,没走近我们。
日复一日,各拉丹东雪山渐渐远去,离目的地——沱
沱河大桥越来越近了。
这一天,我们终于驶离网状水系,江水在两座山间急
转方向,进入山高水深的峡谷地带。长江,你从雪山走来,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朝向大海,滚滚东流。
江边兀立一座嶙峋的褐色石山,上面斑驳的遍是鹰的
灰白色粪便,原来是一座“巨无霸”的鹰巢!我们的到来
惊起数只雄鹰,在半空盘旋不去。
抬头久久注视着这些江源守望者、长江的见证者们,
渐渐地从心里只留下虔诚的祝福。而此刻,谁是真正的征
服者和被征服者已不再重要了。鹰啊,也请你为我们,这
群世纪末的来者作证。
1998年9月26日下午5点,沱沱河大桥终于出现在我们
的视线中。
不知是眼前久违了的景象还是身后告别了的无人区,
使我们的视线变得朦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