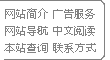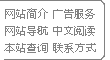魂断黑竹沟——谨献给离开我们两年的车少阳
文、图/闫 琪
这是块静躺了数十年冷得发抖却又被新闻界炒得滚烫的地方,这
里曾发生多起人畜入沟神秘失踪的事件。
当地有诗云:黑竹沟,黑竹沟/十人提起十人愁/猎犬入内无影踪/
壮士一去不回头。由于它神奇的和百慕大处于同一个纬度,因此国
内外舆论界称之为“中国百慕大”、“恐怖的死亡之谷”、“神奇的
魔鬼三角洲”。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小车的离去,是为了换取我们8个人的性命!
车少阳是我的大学同学,去年12月24日是他两周年的祭日,在越来越
临近那个日子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就越来越清晰地一次次出现在我
的脑海中。
那是1994年的寒假,我们九个北京体育大学的小伙子在一片冰天
雪地中闯入了号称“中国百慕大”和“死亡之谷”的四川黑竹沟,没
有资金,没有丰富的探险设备,也没有专业探险经验,我们只有年轻
人特有的执著与冲动。 当时的黑竹沟还是一片几乎无人涉足的处女
地,它地处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小凉山地区,位于东经102°、北纬
29°9′,与百慕大魔鬼三角、埃及的金字塔等一些神秘地带几乎处
于同一纬度,而且这里同样也出现了一些人畜失踪的神秘事件,在当
地彝族山民中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传说,加上新闻界的炒
作,使黑竹沟显得更加幽深莫测。
几经辗转,我们终于来到了黑竹沟。很难说得清当时是怀着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的人生阅历加上精彩的一笔,也许
是想体验一下那种恐惧后的快感,也许只是为了证明一种什么东西。
其实人生不就是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在寻找着一种东西吗?这种
东西有时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它可能就是一种精神或一种感
觉。但最重要的是:黑竹沟,我们来了!
当地县政府给予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不曾想到的,一顿极其
丰盛的彝家饭菜和彝族兄弟的动情歌声使我们在进沟之前从体力上和
精神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补充,随后在两名当地最好的猎手带领下,
我们迎风踏雪闯入了那一片莽莽丛林。
黑竹沟属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山地的高度地带,它背倚盆地边缘
的马鞍山,北邻大渡河峡谷。该地区山势险要,地质构造复杂,地貌
类型多样,既保留有角峰、冰斗、刃脊、V型谷等第四纪冰川遗迹,
又具有复合漏斗、暗河、深谷、峭壁等喀斯特地貌特征。从地质
史上讲,这里由于遭受第四纪冰川的袭击相对较小,使许多古老的动
物、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最著名的如大熊猫和珙桐。另外沟内毒蛇猛
兽众多、沼泽暗流密布,以及传说中的神怪、野人都使人不寒而栗。
冬季的沟内阴暗晦涩,迷雾缭绕,阴风惨惨,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
尽管水声震耳,却仍让人觉得静寂得可怕。我们随着向导,先趟过一
条从黑竹沟腹地流出的三岔河,然后在冰雪泥泞的林间前进,由于没
有轻便的睡袋、睡垫,我们就背着沉重的被子和褥子,那么我们就不
得不将食品和其它必用品压缩到最低限度,即使这样,每个人的背包
仍然十分沉重。大约七个小时以后,第一天的行程结束了,我们在一
个山崖下扎下了营地。在扎营时,我们曾看到对面雪坡上跑过两只可
爱的小熊猫。营地扎好时是傍晚5点多钟,此时沟里已是混沌一片,
黑暗之中裹着浓雾,空气潮湿得似乎要滴出水来。出于大强度的行军,
每个人的衣服几乎都已湿透,随着沟里一阵阵阴气袭来,令人难受得
不可名状,虽然点起了篝火,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的晚
餐仅仅是一些热汤加四块压缩干粮。为了保证第二天的体力,在可怜
的晚餐后,我们必须进帐篷休息了。我们九个人分成三组轮流守夜,
我、小车和杨新利是第二组,排班从0点到3点。我们三个湿漉漉地钻
进了帐篷,裹着湿漉漉的被子躺在湿漉漉的褥子上面,甭提多难受了。
我们呼出的热气在帐篷顶部凝成水滴,偶尔滴落在脸上,就一下凉到
骨头里去。我像睡在一片沼泽里。为了给明天储备精力,我只能强迫
自己去睡,昏昏沉沉地徘徊于半梦半醒之间,而我身边的小车蜷缩身
体瑟瑟发抖,他肯定更加难熬。其实昨晚睡在林场的时候,他已开始
感冒,但12分钟能跑3200米的足球班的他根本没当回事。是的,像我
们这些体院的大学生谁会将这区区感冒放在心上呢?
黑暗中,我能听得见小车的上牙与下牙相互碰撞发出的声响,还
能听得见小车用一种颤抖、含混不清的声音和我说话。我记得他对我
说:“我真希望守夜,那么就可以烤火了……我现在就是‘卖火柴的
小男孩’,烤着温暖的壁炉,吃着叉满刀叉、流着肥油、冒着热气的
烤鸭……”他还是那么幽默。我于半梦半醒之间应答着:“梦到就能
做到,你能看到你就去吃吧,别管我们。”冰冷中,我和杨新利不约
而同地抱住了他,但仍然止不住他的颤抖。
长夜难熬,黑竹沟的长夜更加难熬。
终于该我们守夜了。坐在篝火边,喝了点儿热水,吃了几片感冒药,
小车的精神好了许多。守到3点钟,再钻入“沼泽地”时,感觉似乎
比刚才好了许多,我睡着了。睡觉时就是体力恢复最快的时候,可后
来听小车讲,他始终没有睡着,他仍然是在恍惚中“烤着壁炉、吃着
烤鸭”。
天终于亮了,由于食品匮乏,早餐定量比昨晚减半,每人仅吃两
块压缩干粮。吃完早餐后,准备上路了,向导说前面的路更加难走,
背着这么沉重的被褥、帐篷恐怕很困难。据他们估计,如果轻装前进,
大约中午时分能够走到黑竹沟的腹地,也就是最险恶、最恐怖的石门
关。以前富有经验的地质人员、解放军测绘兵都是在石门关附近神秘
失踪的,据说在石门关附近一旦发出声响,就会有毒雾从石门关中涌
出将人畜包裹,等毒雾散尽以后人畜将不见踪影。向导建议,最好将
辎重留在这山崖下,轻装前进,到石门关附近勘察一下后立即返回,
能在天黑以前返回宿营地。两名向导坚决反对我们进入石门关,他们
说到了石门关附近他们绝对不会再往前走。我们经协商后,鉴于食品
的匮乏和装备的简陋决定采纳向导的建议,于是我们就带了点儿吃的
和一些必用品出发。
我本想提出小车生病的问题,但小车坚决不让我说,怕影响队伍
的整体性和士气,我也觉得在这片迷雾重重、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里,
将小车一个人或几个人留下那简直太危险了,小车又一再说他没有问
题,于是全队向黑竹沟腹地出发了。正像向导所说的那样,今天的行
进的确比昨天更加困难,开始是逆着三岔河往前行走,河滩上巨大的
鹅卵石上结了一层薄冰,极其光滑,随时有崴脚、滑倒的危险,大家
小心翼翼地走过这段河滩,向山上爬去。钻入了丛林,向导在前面用
弯刀开着路,仔细寻找许多年以前他们进山寻找失踪人员时留下的路
标和痕迹,而且两人不停地商量着什么。此时我们位于三岔河河谷的
边缘,基本上是沿约有60度的陡坡横向前进,脚下几十米处就是奔腾
咆哮的三岔河,脚下的路十分狭窄和泥泞,我们都尽量用身体向内贴
住山坡,手中不断抓着身边的植物,确保自己不会滑下去。两个小时
后,我们离开了河谷,开始翻越一座接一座的雪山。在一个雪山的山
脊上有一大片被压倒的竹林,向导指着一些粪便和脚印告诉我们,这
是大熊猫留下的,而且还是最近一两天刚刚留下的。这时已经是中午
时分了,向导说离石门关已不太远。我们在此做了短暂停留,每人吃
了两块压缩干粮,然后继续赶路。出发前向导一再叮嘱我们现在已邻
近石门关,切记不要大喊大叫,防止出现毒雾。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队形保持得很好,每两人间的间隔距
离都在四五米左右,每翻过一座雪山我们都禁不住问向导还有多远,
向导总是说快到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坡就到了。然而翻过那一座雪山,
前面仍然是下一座雪山,此时密林中的雾已越来越浓,七八米以外几
乎看不到人影,四周沉寂得令人窒息,每个人都被浓雾包裹着,能听
得到自己的心跳和沉重的喘息声。我们为了防止队伍脱节,前后互相
呼喊着,但立刻被向导用低沉的嗓声严厉制止,这两名原本和蔼可亲
的彝族大叔现在脸色相当严峻。我们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再也不
敢乱喊了,只是跟着向导往前走。队伍逐渐分为两部分,我和三个队
员紧紧跟着向导走在前面,不知不觉中小车和另外四名队员已远远地
落在了后面。
下午2∶30的时候,浓雾中远处后方传来他们焦急的呼喊,让我
们停下。过了好长时间他们五个人才赶了上来,原来这时小车已经有
点虚脱,实在有点跟不上,而且咳嗽得厉害。有一名队员说现在小车
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往前走了,必须立即往回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有的队员认为现在已经离石门关很近了,如果连石门关看都没看到,
那么这次探险就算失败,还是希望最后冲一把,也不枉千里迢迢来此
一趟。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问向导这儿离石门关到底还有多远,向导
只是说估计不太远了,这个方向没错,但他们也是好多年以前寻找失
踪人员时走过,当时留下的路标有的已找不着,而且当时也没有这么
大的雪,所以估算的时间才会有误差。他们说尊重我们的意见,但希
望我们能快下决定。在两种意见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情况下,最后决定
我们九个人举手表决,表决结果——5∶4,往后撤!
当时我还傻傻地举手要求继续往前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实在
是太冲动了,石门关还要走多久很难说,没有任何露营的设备,照明
设备十分简陋,每人的食品只是几块压缩干粮,大家体力都已消耗得
差不多,小车更是连累带病已近虚脱,一旦天黑下来,被困在这冰天
雪地的“死亡之谷”中,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也许会全军覆没
!多么庆幸的5∶4!
我们沿来时开好的路迅速后撤。现在小车让我们非常担心,他开
始发烧,神志已不太清楚,一路跌跌撞撞。由于路极窄、极险,我们
也无法背或架着他,只能在他前后尽量照顾他,回来时,我一直走在
他身后,许多地方相当危险,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他却意识
不到,竟敢跑过去,后来我们开玩笑还总说当时他是打着醉拳回来的
。虽然总是有惊无险,但吓得我们出了一身身的冷汗。天色很快暗了
下来,行进更加艰难,大家借助仅有的一点儿照明工具摸索前行,黑
暗无形中增加了人心理上的恐惧感,让人觉得在黑暗中再也走不到尽
头,每个人都是连滚带爬,下雪坡时都是屁股一坐,一滑到底,雪水
和着汗水使每个人的衣服都已湿透。终于,我们回到了宿营地,那时
已是晚上快9点了。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精疲力竭的身体渴望着
休息。再看小车早已倒在帐篷里连动都不想动,他太累了。由于没能
找到足够的干柴,我们没有点起篝火,只是用酒精炉烧了一点儿热水
,吃下几块压缩干粮,然后都钻入了帐篷,虽然被褥更加潮湿,几乎
能挤出水来,但我们在极度疲劳后,都沉沉地睡去,只有小车时断时
续、连心彻肺的咳嗽声回荡在阴森森的“死亡之谷”……
第二天大家9点多才纷纷起来。小车发烧更加严重,额头烫得吓人,
有时咳得似乎要背过气去。早餐仍然是入口难咽的压缩干粮,然
后大家收拾行装准备出山,浸了水似的被褥比来时沉了不止一倍,几
天来大家体力极度消耗,又几乎得不到营养补充,再也背不动了,最
后只得将被褥扔在了山里。我和杨新利一前一后照料着小车,大家于
饥寒疲惫中有点儿狼狈地向山口走去。又是六七个小时极其艰苦的跋
涉,当我们趟过冰凉刺骨的三岔河,爬上山口的公路时,大家不约而
同地躺倒在地,回头望望刚刚走出的这一片迷雾缠绕的山谷,我心里
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又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结束了这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后,我们告别了淳朴好客的彝族同
胞,各自回家过年。我从来不认为这次探险活动是失败的,这绝对是
我一生中极难得极精彩的一次体验,它给予我心灵的震撼将是我一生
受用不尽的财富,一个人能够享用最好的同时,也应该能承受最差的,
能在生死的交界处走过一回,人将会对生命、生活多几分感悟,将会
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当我们再开学时,我们没有见到小车。回家后,他被诊断为肺结
核,休学一年。后来听说病情一步步恶化,先是转化为胸壁结核,再
后来转为癌变,由于家乡大同医疗条件有限,他转到北京通县的肿瘤
医院治疗,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他还回学校来看看我们,再见到
他时,我几乎落泪,原来瘦削精干的他由于化疗和注射激素,头发几
乎全掉了,整个人也浮肿了起来,只有他的精神还是那么好,他还开
玩笑说黑竹沟把他折磨成这样,只要死不了,总有一天要去把它的老
底揭穿。我们毕业时,他还专门从医院赶来送我们,那是我们见的最
后一面。同年12月24日,就是在这个西方人所谓的平安夜里,他终于
离开了我们,死因是淋巴癌,全身的免疫系统都被破坏了……
事后我们几个每每再说起那次经历时,都唏嘘不已。毫无疑问,
当时若不当机立断迅速回撤的话,绝对凶多吉少,其实那几名建议往
后撤的队员当时体力倒没什么问题,他们也真想亲眼看一看那座神奇
古怪、被彝族同胞视为魔境的石门关,他们主要是考虑到小车的身体
才下此决定,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小车没有病得那么严重,举手表决
的结果就不会是往后撤,那么全队只会在那片“死亡之谷”中越陷越
深,很可能全军覆没。冥冥中是小车用他的生命将大家的生命从“死
亡之谷”中拉了出来!
是的,是小车用他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了我们八个人的生命!每当
临近“平安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总会想起小车,想起黑竹沟。我
真希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够再次闯入黑竹沟,揭开“死亡之谷”那
神秘的面纱,为了自己,也为了小车;也希望小车在那个世界里仍然
能够保佑我们。
祝小车幸福、平安!
(栏目编辑:马小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