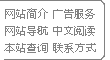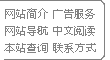Customs
藏区有个人新村
是一辆运输卡车,没有篷布,可望天,可看地。
从然乌湖出发,先在湖滨公路上开开停停,人们上上下下说说笑
笑,很热闹。然后过了康萨、曲呀、屋鲁堆才安静下来。
一路颠簸,山回路转,车上就静默了许久。无人区的山野旷路过去,
便开始翻越德母拉山口,气候骤变,寒冷得个个目瞪口呆,就尽量挤
得瓷实。
路,高盘了几弯,灰湿的迷空纷纷扬起雪花绒,飘逸不落,舔一
舔丝丝的凉甜。又一会儿变成雨加雪,再一会儿天就晴了。
车,开始在狭窄山谷中穿行,抬头见蓬蓬茸茸的高崖倾悬,掩饰
着半扇晴朗迷乱的天空。此时车上的人们极其安静,似乎惧怕再添加
个声响就会惊塌脑袋顶上呲咧的岩石。
葱茏簇拥着的察隅县城,小却极是安逸。主要是一条北高南低的
坡街,长不过二里地。街西便是哗然南去的桑昂曲。其实公路过德母
拉山口后,一直沿袭桑昂曲河岸。
在县城,我们换搭一辆运木材的卡车,穿山越岭,走关卡,过检
查哨所,最后到了下察隅的巴安通边防派出所。指导员宋佳清指派藏
族战士达瓦把我们送到 人新村住下。
人目前属藏族的一支,但我们在县里采访得知,他们和藏族几乎
没什么关系。人口约有1000多人,生活繁衍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额
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上,位置
是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西部的高山峡谷区;南临印度,东
接缅甸,西连珞渝,北靠藏族地区。北部高峰达5000米,但河谷地带
海拔却只有1000多米,属山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北部群山像北京四合
院一进门的影壁,既挡住了北面的西藏高原的寒流,也迎接住印度洋
的湿润气候和丰盛的雨水。因此这个地方夏无酷暑,冬不严寒,一年
的温差很小,每天的温差却较大,气候性格很是鲜明。每年2—9月为
雨季,10月至来年1月是旱季。此时我们的 村之行,赶上了一个雨
季的尾巴。
一路上,小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海拔高低,植被分布是垂
直的。雪线下是高山草甸低矮的灌木,再往下是大片大片的云南松林,
河谷地带是阔叶林,有榕树、青冈、竹子和野芭蕉等等,枝叶繁茂,
很少看到裸土。这里还是藏区著名的原始林,储量为1亿多立方米。
林中野兽不少,除了熊、猴、獐、小熊猫、野猪外,还有野羊、野牛、
虎、豹……以及种类繁多的飞禽。
公路上看河谷两岸,开阔的台地上是成片的梯田,景致很新鲜。
快到巴安通时气温更高,温度更大,路边河畔闪现棕榈和一些叫不出
名字来的热带植物。水果也多,香蕉、柠檬、柑桔、苹果……
人没有文字,大多使用的是结绳和刻木记事的方法。平时没有记
年月日的习惯,因此也就无从谈起生日和年龄。
他们的竹木制作手艺不错,小到饮水器皿,大到窝居。路上见的房屋
,
低杆栏,离地一米左右,不用地基或柱石,只用木桩,四壁是木板咬
紧,房顶用藤条毛竹铺盖。我们去的人新村,木屋相似它的友邻墨脱
县珞巴、门巴的住房。他们之间虽然大山丛林阻隔,但这房屋建筑表
明生命的坚韧不懈和交流的顽强。想当初我们的察隅之行,是计划从
墨脱翻山越岭东走原始林,然而面对浩瀚的没有人迹的山林,面对门
巴、珞巴猎人赤脖红脸的劝阻,我们胆怯了。
其实那是一条极其精彩、极其美妙、极其艰苦、极具磨难、却也
极具诱惑力的探险之途。
察隅全县总面积为9600平方公里,恰是我国领土的千分之一,距
拉萨900公里,距成都1500公里。县城距318国道172公里。这172公里
就是我们从然乌湖到县上的距离。
人新村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坡坝上,我们住在村长家的一幢二
层木楼,与村长住的木屋南北间隔50来米,“院落”里野生着一些花
草,盛开着粉红和白色。
村长的木屋门楣以及灶塘大屋西墙,挂着许多驱鬼避邪的兽类头
骨,幽暗的塘火照在上面,它们似乎在眨巴眼睛。
一日上午,玉米地的西边,传来法器和念经声。问村长,他说,
那边屋头死了人,正在做驱灾降鬼仪式。我说难得,要进去看看。他
说仪式开始,36小时不能有人出入。我们不相信,钻过玉米地来到这
家木楼前,却被无语的冷漠制止在屋外。
我不甘心,让尼玛找来了一个叫“超”的中年人给我们介绍了一番。
人死后,将尸体弯曲成胎儿状,用竹席或布匹包扎缠紧,在自家
木屋西(约9米)边,搭一竹棚,死者在内停放四日五夜,其间巫师念
经(许是超度经?),五夜过后的凌晨,抬出尸体远离居住区,架柴火
葬,又两天两夜后,家人亲属再去掩埋死者灰骨。“超”说,南边的
●人葬礼,也有的是将尸体弯曲捆扎后装进圆木挖的树槽在高坡上掩
埋,埋葬前在死者身上系一根麻绳牵出地面,365天后,死者家属再
来扯动绳子,若绳子扯出,即死者离去;反之就要挖出尸体火化后将
骨灰埋葬。
那天早晨,从我们居住的木楼前,看见南面几百米远的山坡上,
火葬的浓烟团团滚滚,像座飘升的青砖灰塔,托举着一个灵魂进入了
天堂。我还是要去看看,村长磕打着长银管烟锅,长出了口气摇摇头,
止住了我的脚步。他的一声叹息,似乎是对生命短暂的谴责和无奈。
人的衣服也是蛮有特点的,男人有头盘,穿没袖的长衫;女人着
色彩鲜艳的短衣和花裙子。“超”说,早年无论男女都用长长宽宽的
彩布,从肩膀围绕在腰间,白天当披裹,晚上当被褥。所以过去流传
这样一句话,概括了 人的生活:“正午鸡爪谷,睡觉靠块布”。
十来天的交往,发现他们甭管男女都喜欢戴银饰,妇女耳垂更甚,如
同小喇叭,更像云南的铜鼓,坠得耳朵又大又长。
在村庄的中央位置,也就是村长家的北边,有一个棚院,那里有
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热闹非凡。其中聚集着一批约五六岁
到十几岁没父亲的孩子。早早地来,晚晚地走,他们基本上是外来男
人和本村姑娘私生的,成群结队像过集体生活。尼玛说,他们的父母
有的同居数月半年,有的三年五载,但最后男人还是走了,把孩子和
艰难的日子留给了女人。好在这个部族、这个村庄并不嫌弃她们,否
则她们的境况可想而知了。
这其中也有个别感情较好的,孩子已经六七岁,男女双方还是和
和睦睦。我挑了一个午饭后的空闲,专门走访了一户三口之家。进得
这家院子,男人正在菜地里忙碌。他是汉族,32岁,老家在四川省沱
江,1985年夏季来这里做木匠,老实巴交的不爱说话;女的,估计20
多岁,高挑周正挺漂亮,是本村土生土长的 人后代,读过两年小学。
我看他们家比较窄小简陋,女的快人快语,说不想盖新房,想再攒点
儿钱,跟男人一起回四川定居,说他们去年已经回去过一次了。又笑
着说,虽然没觉得四川的土地比这里的怎么好,但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吧。
你俩没领结婚证吗?我问。女人说,那东西不管用!我觉得她说的
也对。
据说这个村庄新建时间不是很长,原因是许多 人从深山老林搬
来住得不习惯,就又搬回去了,多次反复才算安稳下来。政府为此也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县委办公室王怀主任,用了半天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了察隅县的情
况。这里真是一个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风情浓郁的好地方。最后他
希望我们多为他们宣传,为贫穷落后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欢迎
游览、欢迎开发、欢迎投资。
我们又拜访了几户人家,发现 人的服饰比门巴、珞巴保留得还
多、还丰富。我们请村长协助,在白天组织了一个联欢会。篝火晚会
当然更好,但选在白天,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摄影机需要光亮,没有照
明,拍出来也没效果。
他们的舞步较简单,男男女女一个尾随一个,很像北京早年交际
舞中的“拉龙”,弯弯曲曲转来转去。乐器是一鼓一锣,有点锣鼓喧
天,但节奏缓慢。婚后的女人几乎都抽烟,以旱烟为主,银制的烟袋
锅有花纹图案,精美漂亮。
这里是一处安居人生之所,让人惜恋。告别这幽静宁和的村庄,
我们包租了一辆212吉普车返抵察隅县城。车上一共是10个人。要去
县城的老乡太多,而车又少得可怜,没办法,挤吧!
吉普车在山路上以50迈的速度行驶,我睁开眼睛,从身边一位老
人的肩膀上看出窗外。公路下是弯弯曲曲清澈安谧的桑昂曲,往上看
是郁郁葱葱的绿林,再高就被变化莫测的白云山雾笼罩住了。
倏地,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原来老人双腿间站着
个六七岁的男孩在吃生毛豆。我向他张张手,他就递过一大把,
数了数一共5个豆荚。剥了吃,车厢里的清香气就漾得满满的。一个
小媳妇,抱着个吃奶的孩子,白白的大乳房遮住娃儿半张脸,随着车
辆,她哼起了 人小调,那音律有点像藏族围着锅庄跳舞的“旋子。
车速似乎更快了。突然,我的心在目光的牵引下紧张到极至。车的前
方几十米处的公路被山上的洪水豁开了一条数米宽的大沟。然而此时
此刻司机的发现已经于事无补,煞车是绝对来不及了。那一瞬间的我
却丝毫没有恐惧,只是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后果。车速没有减
慢,这让我有了一种错觉,司机似乎没有发现前边的断沟。
其实不然。当我感到司机的抉择时,我在心中为他叫好。那一时
那一刻令人兴奋异常。
车子加大了油门。
一点不夸张,我睁大眼睛目睹了我们的车子飞起落下的全部过程。
那是一种灾难临头的冷静;那是一种对灾难恐惧到尽头的不屑;那是
一种不考虑灾难本身,只等待灾难结果的祥和……吉普车微昂着头,
像一枝飞出的箭,冲向沟的对岸。但是那沟太宽了,只是吉普车的前
轱轳搭上了沟沿。
此时我脑中闪过命掷于此的念头,但马上消失。我们在任何艰难
险阻面前,都要学会——坚韧和绝不放弃,我的心出奇的平静。车似
乎被什么东西阻碍了一下,“哐当”或是什么怪响,车内的人们随着
惯性冲向前去。
我下意识在等待着什么。在等待颠覆、翻转和滚动?在等待着撞
开车门或撕开帆布顶棚?
212吉普车平稳地停刹在大沟的彼岸,停在公路上。
检查:司机和诸位未受大伤,只是我们的同伴,把车子挡风玻璃撞碎,
头部起了核桃大的一个包,他的眼镜也碎裂。一小男孩头部撞在何处
不知,也起了个如同核桃般的大包,其他人安然无恙。真够幸运的。
回首大沟宽约5米,深约7米,大坡下,是不很湍急却很宽深的大河。
车再开起,车下就呲哗呲哗怪叫。都下车去查看,原来是后右轱轳中
心瓦圈铁板翘起。我们将就了十几里地找到一个道班,借了一把18磅
大锤,我小试了试当年做建筑工人时的身手,抡圆了几下,就让它恢
复了原位。
回到察隅县,卸下行李背囊,正琢磨着怎么赔偿212吉普车的玻
璃,司机却惊魂未定,慌慌张张招呼都没打就开车跑掉了。
察隅就更加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栏目编辑:陈力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