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身份带来的焦虑与成长“你是哪里人”
导语:“你是哪里人?”回答这简单问题,在这流动的时代,变得困难。当我们试图找到归属感,试图在身份中寻求意义,焦虑也产生了。而这无法逃避的身份焦虑,其实也是我们探索真实自我的驱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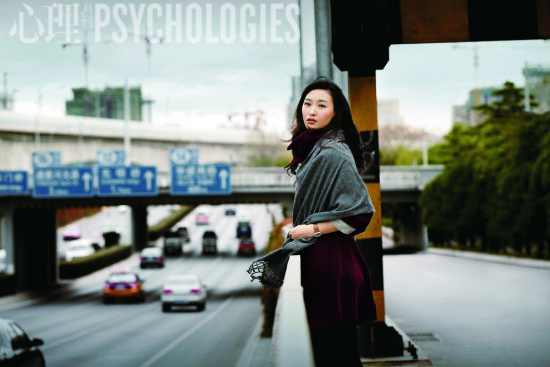 是什么让我们失去归属
是什么让我们失去归属靠近年关,数亿中国人将踏上回乡的路。“过年”以及过年带来的这场不可避免的年度大迁徙,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在“背井离乡”,同时看到中国人传统的强大和执著。何清也年年身处这潮流之中,她总是早早地订好往返机票—她在北京工作,父母在广州,而中国人春节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奔着父母的所在,奔着心底的故乡去。
可是,如果说广州是何清的故乡,她不能同意: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心理意义上也不是。她只是15岁时随父母工作调动到这座城市,一年后她就到上海上大学了,广州之于她,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每当她坐在从白云机场开往市区的出租车上,眼中所见,心底所感,都勾勒出一份无所指向的平淡却清晰的乡愁。
在将近一个半月海陆空总动员的春运中迁徙的数亿中国人,以及更多在居留地过年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像何清一样,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怀抱复杂情绪:离开的可能不是家,去往的可能也不是故乡……
一个难以回答的简单问题
在这个流动的时代,你是哪里人—这个中国人惯常用来开场白的普通提问句,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回答,或即使回答却并不完全认同。事实上,中国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位置和流动方向已经30年了。有几亿中国人在短短的30年里,发生过比较重大的个体生命的位移……我们的个人生活史是由数个城市的生活片断组合成的,要说清楚自己是哪里人,确实不容易。
梁颖就从来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人。籍贯、出生地、成长地、户口所在地分属不同地方……到底按照什么原则回答呢?这么多地方,让她摘出一个她心底里认可同时也认可她的地方,又摘不出来。有时候梁颖会随便说是新疆人、西藏人或是甘肃人,还说过自己是契丹人,她也给过“中国人”和“地球人”的答案。但是更多时候,梁颖的内心会迟疑,无从答起。“一个平平常常问出的简单问题,我却只能开玩笑带过去,其实是有些心酸的。”梁颖说:“这虽然不是个人生命里多么严重的问题,别人不问我也不会怎么想,但是,这么被问得多了,慢慢地,它的确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一个追问:是啊,我是哪里人呢?”
吴子薇的情形很有些不同:3年前,她还是能够清晰地回答自己是哪里人的。她曾在心底里认同好几个故乡:山东,8年成长史;河北,2年少女成长史;天津,10年求学史加2年工作史;深圳,10年移民奋斗史。吴子薇说,在心底拥有故乡,对她非常重要。“在深圳,我有户口,有居所,甚至我是在深圳领的结婚证,但是我总是一个外乡客,我生命中很大一部分历史不在这里,我心底必须拥有我的那些故乡。它们让我相信,即使在这里我很失败,我仍然可以退回到我的故乡去,它们会收留我。”也因此,对故乡的思念,成为她抗拒内心的漂泊感与外在生活压力的精神支柱。
可是当她回到山东和河北,无论她自己还是山东人、河北人,都互相不认为他们彼此“属于”—她和她的故乡,变化都太大了,她甚至水土不服,身上会起一片红点;天津,她心底最后一个故乡,也是她的出生地,可是她离开四五年后回去时,也是物非人也非,更令她感觉荒诞的是,出租司机当她是外地人,大姐长大姐短套着话,却摆开了架势带她绕路。“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在一个你当作故乡的地方!”她气恼地跟司机说着应该走的路线,心底里,青瓷暖玉般被她珍藏的故乡清脆地碎裂了……“我曾经固执地保留着对故乡的记忆和想象,却在与它们一个一个面对时全部破灭,我发现我哪里人都不是!”
 人,从来就是“群居动物”
人,从来就是“群居动物”是什么让我们失去归属?
人,从来就是“群居动物”。马斯洛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心底与故乡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结,即使我们远走天涯。
可是故乡不再是故乡。同样把天津视作故乡也同样失却故乡的崔丹抱怨,是中国所有城市不加思考的“现代化”造城运动让她没有了故乡。曾经承载着她强烈故乡感的老街、老屋、老树都不见了,她的归属感变得无处安放:“真的就漂着了”。连带着造城运动而消失的,还有熟悉的邻里文化以及更多值得回忆的生活方式与乐趣。
让我们失去故乡的,还有我们的自主“流动”——这么多年来,整个中国都像河流一样在流动。现代化的结果是集体不再为个人负责,而是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传统的身份限制被打破,社会流动的障碍减少,移民、换工作、努力升职……人们都在努力追寻、争取更高的身份理想。“我们的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自己主动得到的。特别是当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去哪里、做什么,以及不去哪里、不做什么。我们的父辈,大都是一生与一座城市一个单位厮守的;如今这样的自由让我们有些忘乎所以,当年,有点理想的全都追求走在路上。”吴子薇说。她当年扔掉“体制内”的舒适与安全感,带了1万元钱(她认为至少够半年找不着工作用的)、一个双肩大背包、一口大衣箱,无知无畏地跟随着南下的滚滚大潮去了深圳。“我当时在日记中这样写:我想要人生中可能性的花朵绽放,而不要在必然性的、也就是能够看得见老的人生安排中沉溺。”像吴子薇一样,数亿大迁徙的中国人是怀抱着发现、创建自己人生新大陆的巨大欣喜与冲动和冒险精神,自愿地(至少是部分自愿地)丢失身份和故乡的。
离乡就像一个成长的隐喻
“自由与焦虑难分难解。”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Irvin D. Yalom)说。因为,自由就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行动、自己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
离乡一定带来归属感不满足。心理学家朱建军认为原因有三个:“一是地点依恋,这是人类从动物阶段遗传来的一种本能,就像所有兽类都有固定的领地,人会对自己熟悉的地区有依恋,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会感觉不安全;二是人际的归属感需要,离开故乡的人,如果与同乡、熟悉的人在一起,这种归属感不满足会有所缓解;第三,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较强,从文化教养来说,中国人说起‘背井离乡’会觉得很负性,这也导致中国人离家到新地方后归属感不满足会更严重,而吉普赛人的焦虑就会少一些。”
但是,朱建军认为离乡是我们成长的重要途径。正如不剪掉脐带婴儿就无法成长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成长就是逐渐从群体的母体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朱建军说:“离乡就像一个隐喻,代表着人的成长过程—长大后需要离开原来熟悉的家庭、生活方式,去闯荡,才能使他/她与原来家庭不同的自我成长起来。”30岁才离开陕西宝鸡的宋朝晖对此感触很深,他说自己在北京历练一年,超过在家乡10年:“外在逼迫着你,内在也逼迫着你,一定要特别迅速地建立自己的新生活。这种成长是迅速压缩式的。”
一种探索自我的动力
当我们进入与自己不一致的环境中时,身份认同往往就发生了。吴俊芳说起自己的经历:“16岁到上海读书,同学开玩笑时学我的口音,还有想吃辣吃不着时的思念,让我意识到湖南乡土对我的影响;后来去美国读书,发现自己与周围同学不仅肤色不同,生活方式、思维习惯都有很大差异,才感觉到中国文化已经进到我的骨髓—前20年我从没那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有比较才有真正的了解。往往,我们只有离开生活过的地方,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它,才了解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文化。
所以,对身份的焦虑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坏处。“这种焦虑、冲突也给我们一种探索的动力和思考的方向,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身份、了解真实的自我。”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社会心理学家彭凯平说:“在移动很快的世界里,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不断焦虑,不断认同,再不断焦虑,再不断认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哪些不足,逐步完善自己的。”
在2000年以前,电影导演贾樟柯对北京这座城市一直不适应,没有归属感,但是他说“孤独,我可以克服,只要通过努力的工作便能忘掉这一切”。网易的丁磊也把这种“飘”当作一种磨砺,他认为这过程“不单能从心理上来培养自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让他深刻地明白“越是灵活的人越立于不败之地”。
朱建军比较强调平衡。他说:“离乡对于我们的成长有好处,但是根还应该连着。根连着,就是说不要完全否定自己的来源。否认它就等于否认自己的一部分—内部就有分裂,有冲突。一个健康的态度应该是,承认自己的一切,哪怕是不理想的。这样,自己的一切都会成为自己可利用的资源。”
可以接纳所有的身份
一定要拥有一个明确归属吗?我们的身份焦虑,往往是在从自身当中寻求意义感,而此时,我们也将社会、他人放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上。彭凯平认为:“过分强调类别、身份区别,容易让人产生单向的、狭窄性的思维倾向。所有的分类都是机械的、人为的,从心理上我们可以更灵活一些。”他提倡“多元身份认同”,一种“既此且彼”的关系。“多元身份认同,就是认可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种类,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身份。”
我们也可以在自身以外去寻找意义。彭凯平说:“如果你成为一项伟大事业当中的一部分,就不会再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另一种选择是接受自己“哪儿也不属于”的状态。曾经为身份焦虑的吴子薇,如今已对无归属的身份坦然。她说:“我其实已经由不确定的身份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获得了一种能力——每到一个新城市,我反而能够以更坦然的心融入、观察,也能够比较容易地与新城市建立一种联结。”
杨中芳曾在美国居住15年,这位自称“游走于大陆、香港、台湾心理学界的心理学家”在邮件中与我们分享了她的经历:“我也曾极想‘再做中国人’,在大陆尝试了好多年,最终放弃了,也体会到自己永不可能完全融入本地。因为我的经历,令我‘格格不入’了。那就接受自己总是‘外地人’的身份吧。我现在在每个地方都以‘外来者’的身份存在,但又与当地人以真诚的态度相处。原来在每个地方,‘外来者’也有其优势。最重要的是要本地人知道你在为一个目标奋斗,这个目标是与本地人一致的。随着沟通工具(如互联网)的全球化,人们逐渐可以不以地缘及与地缘不可分的亲缘来作为归属的基础。不管我在什么地方, 都会和固定的一群朋友联系,彼此互相关心。归属感的建立更靠一些个人的因素。”
最终,身份的焦虑可能烟消云散。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所说:“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自发活动。如果个人通过自发活动实现自我,并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他与世界形成结构化整体的一部分;他有自己正确的位置,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不复存在。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积极有创造力的个体,认识到生命只有一种意义:生存活动本身。”
更多精彩,请关注新浪女性(微博)
编辑/文:张茵萍 屋子 图片统筹:李姗 摄影:赋雷(雷摄影) 化妆:付天娇(形象革命)
|
|
|
- 传周杰伦承认昆凌女友身份 马来西亚甜蜜约会(图) 2012-01-09 09:16
- 传周杰伦承认昆凌女友身份 马来西亚甜蜜约会(图) 2012-01-08 21:35
- 传周杰伦承认昆凌女友身份 马来西亚甜蜜约会(图) 2012-01-07 22:38
- 传周杰伦承认昆凌女友身份 马来西亚甜蜜约会(图) 2012-01-06 14:44
- 组图:身份带来的焦虑与成长“你是哪里人” 2012-01-04 17:49
- 15岁少女太早熟害父母焦虑 2012-01-04 17:14
- 男子扮女装KTV陪唱 身份败露被客人追打坠粪坑 2011-12-31 10:48
- 职场女性如何缓解年终各种焦虑 2011-12-31 09:28
- 美一市长承认同性恋身份 被爆花公款买情趣商品 2011-12-19 11:01
- 美人天下华服hold住身份 2011-12-08 1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