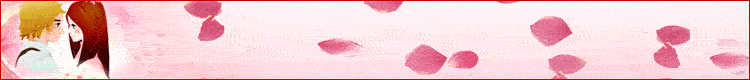作者:楚天
一觉醒来,忽而中产。
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
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1月19日《华夏时报》)
按照这个标准,笔者,以及笔者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产,只不过是在中产的边缘,仅仅在收入一项,就游弋在标准的底线附近--一个月挣三、四千的成都小伙子、一个月挣五、六千的深圳小领(至于领子是灰是白就说不清楚了),睁着惺忪的双眼,黑白颠倒地工作,每月领取工资时钱包看上去倒也鼓胀,但月底总会有一堆不期而至的账单--这群七十年代生人并非总是挥洒自如,与多数时髦的消费方式也基本绝缘,因为房贷、车贷的压力以及“下一代”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教育、生活乃至兴趣培养),使得他们苦口难言。
物质的比较是单向的比较,幸福感的低落恐怕更大程度来自于“仆人感”取代了“主人感”,即对比世界通行的“中产”定位,中国“中产”在社会公共事务上依旧是沉默的一群,他们离自己心中的期望值以及民众对他们的期望值都很遥远。
学者张宛丽提出过衡量中间阶层的七个操作指标: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资格。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就业能力:拥有较高学历,掌握并提供市场稀缺的职业专业技能,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4、职业权力:对其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权,对其上司及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发言建议权。5、收入及财富水平。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以为,七个指标中,最后一项“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实对前面六个指标具有导向作用,才是“中产七标准”的首要标准。如果把中产模式比做令国人心驰神往的一瓶白兰地,那么“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起盖器,只有打开这个封口,美酒才能喷涌而出。
一个说滥了的“中产”的妙处是“中产乃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基本认同现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管理模式,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乐意于维持其秩序。不过,既得利益不应只局限于物质层面,收入也不是权益的全部。在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级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既会对少数富豪群体、官员群体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时刻警惕富豪与官员群体的结盟,防止这些掌握权力与金钱的人操纵社会的发展方向;又会出于学识、良心与利益的综合考量,时不时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言,因为许多中产阶级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从贫寒乡村进入CBD区的。他们的根依旧留在父辈的血缘沉淀中,他们从小身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都促使“中产”们对“社会责任、政治意识、文化建设、道德中坚、慈善公益”等名词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们也清楚地知晓:如果社会无法形成一个朝“帕累托累进”(即让大多数人受益)努力的制度,稳定就无从谈起,社会价值观就会分裂为不共容的两极,不公平带来的震荡会扭曲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所以,理想中的“中产”是“好的制度”坚定的推动与维护者,他们期望拥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发言权,期望“好的制度”能构建一个阶层流动的社会,凭借学习、努力而不是权势的世袭;凭借同一个起点的打拼、竞争而不是“超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的悬殊落差,打通更多的向上通道;他们更期望在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制定过程中,“中产”们、富豪们、官员们乃至弱势群体们都能够有发言的桌子,所形成的任何社会公共制度都是经过多数人同意而不是少数人拍板的……
好的制度让穷人变富,坏的制度让富人变穷。“中产”的诞生需要一个中产的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越来越多,“中产”自然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