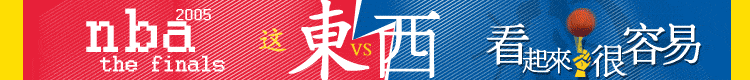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
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
“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色相当专制粗暴。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鸡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
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
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
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
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母亲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母亲总是很坦然,所以,当她仅仅在内心发生了丝微的变化,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作为一对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脐带将我们一直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父母和孩子在某一个时刻会发生角色的互相转换,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充当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这个时刻到了。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