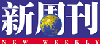窦文涛说王朔:他唯一绕不过去的是女儿
阅读提示:王朔在书里明说,他的一生很明确,为自己,可这态度唯一绕不过去的是由己所出的女儿,在女儿面前他无地自容的心都有。

《新周刊》:你跟王朔熟吗?
窦文涛:以前碰见过几回,跟着大伙儿亲切地叫他“王老师”,也没好意思多说话,不算有交往。我真正识得王朔应该还是我们一起做《锵锵三人行》,那五集节目流传甚广争议不绝,搞得我事后还在电视上两次道歉,王老师痛快了,留我在那儿给观众赔不是(笑),后来他玩笑说“你那节目现在是一盏红灯了,也是我的光荣,咱正经小名叫王锵锵”,我给他回信息:“有了王锵锵,才有红灯记”(笑)。其实《锵锵三人行》有错也有冤,那些个狂人狂话是他在别的场合说的,最后全栽我们头上了,我敢说他在那五集节目里说的基本都挺正的,讲国共两党军官子弟的生活,讲当年他经历的电视剧创作,讲作家的文字感觉,有些骂人的话我们都剪掉了,所以当时批评最有力的就一条——说话带脏字。
《新周刊》:王朔上了《锵锵三人行》,你觉得效果如何?还想请什么人上锵锵?
窦文涛:后来我看见有报道说王朔在节目里一个人滔滔不绝,文涛和文道都插不进嘴去。还有批评我主持不力,不遏制王朔,纵容他砸我们的场子。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没错,这就是某些人,如其然如其然,他们就是这样看人看戏的,砸场子,这可真是城门楼子(俗语,似驴唇不对马嘴之意),像王老师这么会聊天的人,愿意上锵锵,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这叫砸场子,我这主持人无任欢迎嘉宾都来砸一砸。甭说这本是他的说话习惯,即便他少说,也该请他多说,《锵锵三人行》这两年有变化,从“老友记”到打开门多请新嘉宾,好不好另说,但新嘉宾来了,在情在理我们主持人和老嘉宾都会有个默契,我们少说让人家多说,因为人家只来一回,象这样的“聊天式人物访谈”如今几乎每周的《锵锵三人行》里都有,比如崔健比如白先勇比如一位女律师,讲话都不比王朔少,怎么没人挑剔谁说多了谁说少了?关键在于有的人对王朔的“范儿”不喜欢,或者说他出言不逊的狂狷劲儿吧,有人骂他怎么气焰如此嚣张(笑),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老师平常可真不是那样的人。
他是有小孩子气,或者说他选择保持孩子气,但有时候又心细如发温柔体贴。我们有个女嘉宾查建英跟我说王朔这人特逗,查建英反对王朔的一些观点,王朔就说查建英你可以在节目里批驳我,可查建英批的一些话王朔听了又不高兴了,就诅咒发誓跟她从此绝交,查建英想绝交就绝交吧,可过不了俩月,王朔又请查建英到他家修好,还专门给她煮了一锅肉伺候着。
就连批评我们的报社评论员后来上锵锵也反复说明,王朔可以随意媒体不能随便,他批评的只是我们节目组应该把脏字粗口剪干净,但他都说王朔锵锵的内容很精彩,还赞叹他得看多少书啊满嘴跑知识。我倒觉得王老师看书多也不会太多,因为他自己讲过,跟作家阿城相比,阿城是知道十分只说一分,他是知道一分敢说九分。别的我不懂,但在聊天方面我对他们两个相当佩服,叫他们“老师”是玩笑也是诚心。上次听阿老(阿城)聊天,我发现自己简直都成了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句话,多少妙语多少奇闻多少灵感,就在三五朋友人仰马翻的笑声中消散了,不留一些痕迹,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完了就完了。那评论员还说我原来以为最能说的是你窦文涛,看王朔才知道还有比你更厉害的,我说何止王朔,我幸运的是认识了一些真正有才的人,让我明白我虽然整天恬着脸在电视上晃,其实没多大真本事。比我更会主持节目的人,退出了最火的节目,比我更会说话的人,宁愿躲开聚光灯,在私底下博朋友一乐罢了。我实在很普通,多向人家学习吧,其实这样我最安心。
《新周刊》:那你刚才说的道歉是否有点口服心不服?
窦文涛:我刚才说第一反应是不服,可回家里扒开心看看,又不能不承认我是有点偏心眼儿了,人家批评也有道理。这偏心眼儿打哪儿来的呢?还是因职业成偏好的说话癖,我生活里不是很能聊的人,节目里聊的水平也总恨自己不济,老想求进步,结果自己话还是说不好,倒成了个听人聊天的爱好者。王老师聊天个性感极强口语感极强,富于感染力蛊惑力(笑),当然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比方他的某些想法,比方他要说快了有些南方人不一定全懂,还有人可能不习惯他有时光顾一个人说得痛快;可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听他聊,我就见过一伙朋友兴致勃勃围着他,听他一个人连续侃了几个钟头,什么话到他嘴里都能说得特好玩。
我假模假式评一评啊,比如说他在锵锵里侃,我发现在短短一段话里能够事、理、情、趣兼备,末尾还抖出一包袱来,主要还不是刻意做作,那没劲,他是随意挥洒,甚至可以说有点童言无忌,我为什么不打断他?说实话我舍不得打断他,当然不好这么比,但这就像说你特想把一种罕有而奇妙的民间玩艺儿全汁全味地介绍给观众,所以我也老实招供,不怨我们的编导,是我有意地保留了几个脏字,怕全剪干净了会破坏这口语的原味。你瞧我这是琢磨什么呢,一霎时忘了这不是特定观众的艺术电影院,这是给所有人看的电视台,虽然咱也没新闻法,分寸这事我们一向靠感觉把握,但规矩应该是不准出脏字,我错了,确实该道歉,到今天一直剪得干干净净,所以有时候大家看见嘉宾光张嘴不出声,我告你那是他骂人呢(笑)。
必须明白不是所有观众都跟我一样的,比如有的观众会联系王朔在其他场合说的一些话批评他,可我就没太注意,这是因为我平常看人看事的基本态度。我有学习能力,但是鉴定能力有严重缺陷,比如看大片,其实说好说坏我都得先问问大家伙儿怎么说,要你们都说坏,我马上也能说出坏在哪里,可我自己刚出电影院的时候实际心里是恍惚的,因为告你个秘密,什么电影我都能看出好儿来,我进电影院一趟花俩钟头我可不吃亏,这片子再不好总有点可看的吧,故事不好看风景,风景不好看美人,说拍奶子多了那咱就看奶子呗,人家那么辛苦找来,这事我可不自己给自己添堵(笑),不开玩笑,真的,我看什么东西其实角度是非常自私的,这个人身上有些我不能同意或暂时不能理解的地方,那跟我没关系,我只看他身上有什么我可以吸取可以学习的好处,这算不算扬其长避其短呢?过去我认为人是统一的,现在我认定人是分裂的,是个组合物,聚合物,不是一个,是一堆,从这堆儿里什么好坏杂碎你都能拣得出来,人没有内在统一,正在分崩离析。
书也是这样,翻开一页有一段话滋养了你,那就得谢谢作者了,其他的你管那干嘛扔下就完了又不是干评论的,即便一段话的观点你不同意可说得好玩咱也能受点益,比方说你这儿有书,王老师的新书《致女儿书》,里头有这么段话“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像今天依然能看到那样,最愚昧的人活得最好,是一批傻子支撑着人类,或者用阿谀人民的人爱说的话——是人类的脊梁。”——这话要在电视上,可能我得板起面孔上纲上线批驳这不是反人民反脊梁吗?可我私下里读到这儿真实的反应却是给逗乐了,就像听相声乐了,严肃讲对脊梁的看法我过去怎样现在还怎样,只是由此多知道了噢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没听说哪位作家在一本给女儿的小书里就能一言兴邦的,一言乱邦更别想。当然有人愿意严肃也可以发表文章反对、争论,这就是我理解的言论自由。反正我承认我有点是非不清爱憎不明,这一直就是我做主持人的一大缺陷。
《新周刊》:既然说到书,如果选一种王朔引为知音,你选写《动物凶猛》时代的王朔,还是写《我是谁》时代的王朔,或者是写《致女儿书》的王朔?请说明原因。或者在你眼里,王朔始终如一,根本就没有变过?
窦文涛:王老师的东西,只要是公开发表的,我大概全看过,有的还不止一遍,我得承认我是他的新老读者之一,这不等于我崇拜他或全同意他,很简单,就是喜欢,于我有益。他早期的小说我迷过,他现在的东西我也是读了又读。只要一个人曾经有一部作品深深打动过我,不管这个人以后怎么样我也丢不下一种好感。就你说的《动物凶猛》时代吧,我二十多岁,本是个老老实实的石家庄孩子当然一肚子不老实,说起来有点没出息,当时看他那些小说的感觉就像终于找到了学习榜样,噢,原来跟女孩不用老憋着,原来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原来能这么跟人贫,原来话可以说得这么好玩!大开眼界。甭管真假,可以说他给我介绍了一种生活,这生活让我怦然心动,当然有人不这么觉得,那就可能还是我心里本来就有这种东西,跟他碰上了。
十多年前我刚主持节目,在电视上还不会说人话,后来到《锵锵三人行》,我决心说人话了,可说人话一人也有一人的“范儿”,当时我很有些口花花,喜欢的说挺逗,不喜欢的说像个痞子,残余形象流毒至今。这从根儿上讲,其中一个影响得算跟王朔小说里学的,当然人不是那个意思是我学歪了(笑),就这点说还得跟王老师鸣个谢。不过我后来收敛了,因为人在变,一直在受不同人的影响,也在一直审查自己,觉得那也不全是真的我,就是舒服也不能老演流氓吧——(你看,这个句子里就有王朔语言曾经对我的影响)。
其实他如果还复制那种早年的小说,我可能还不喜欢了。到《我的千岁寒》,我的感觉是爱看,甚至看了两遍。你这算杂志访我个人,我不必敷衍,我知道很多人说看不懂,很多人说太差了,可我总不能因为别人都说不懂我明明看懂了愣跟着也说没看懂吧,不能因为好多人说太差了我明明不这么觉得也得跟着说太差了吧,事实是我全看懂了,字字句句看得分明。有人说非得吸毒才看得懂,我倒不这么看,都是中国语言文字有什么看不懂呢?恐怕还是说看懂了可我不懂他写这些个乱七八糟干什么。
有的评论是说得挺内行的,我听着也有理,可问题就在我是一普通读者,文学很浅薄,说实话近年基本没读过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不懂小说该怎么写才算高明,就是说我没背景知识,所以我也不会想到给他排位置,算作品吗?算伟大作品吗?伟大到什么份上?能挤进文学排行榜第几名?还是不入流?这些事我全外行,所以你说它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诗?小说该怎么写散文该怎么论?他这算不算文学?我不管这些,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片片文字,我就是走廊地上看见一纸条也会捡起来瞅瞅,上面的字要有用我就记住没用就扔,过去不听说法国一小说家出一新小说都不装订,一页页就装一盒子里,你可以象打扑克一样随抽随看,你跟他怎么聊逻辑谈结构呢?
所以应该这么说,他这东西在大家的标准里究竟好不好?我实在不懂,但我个人从中确实得到趣味得到营养,甚至有的地方还有小感动,大概因为作者思考的东西我也正好在学习吧。确实不是给所有人看的,现在谁出书又能让所有人看呢?多少而已,现在是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时代吧,什么人不出书呢?各花入各眼,如果不考虑卖钱,有人看就够了,我一点也没鼓励别人去喜欢这书的意思,只是说价值暂时是因人而异的。
《新周刊》:王朔说这几年找到的思想武器是5本书——《时间简史》、《金刚经》、《坛经》、《杜尚访谈录》与《一个原子的时空之旅》。这5本书你读过么?读后的印象如何?你有没有作为自己思想武器的N本书?
窦文涛:巧了,虽然我们没啥交往,可前四本书也是我这几年业余生活里常看的,后来又看了《一个原子的时空之旅》,西方人特别注意把科学最新发现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让大众知道,历史证明宇宙大发现太重要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每一次新发现都导致全人类世界观改变,一次次把社会推进新世代,甚至印象画派的发生都跟艺术家吸收当时的科学成果有关。我们小时候仰望星空,都会有无穷的好奇,宇宙有边儿吗?边儿外头是什么?十万个为什么都不够,后来长大了,很多人忘了这事了,可我,还有不少人还一直惦记着哪,这不好吗?大科学家都说孩子心中的这份好奇要保持啊,这才是一切探索发现的源头。我也是因为有了这些铺垫,所以看王老师的书能懂,且赞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这么好的文笔把冷冰冰的科普知识描写得那么美,把原子拟人化,带着感情,充满想象力,充满戏剧感。
有人会说他那算科学吗?还夹杂着佛、幻觉以及妄想。信不信都好,他有他的精神世界,但这些东西涉及到一种有人以来就没断过的追问,人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什么会是这样?想这些事好像没用,可我也总止不住去想,美其名曰想这些可以帮助我转变对命运的态度,痛苦啦,挫折了,失去了,每个人都经常吧?怎么能没有疑问呢?连屈原都《天问》呢我们怎么不问?问就会有答案,只能是个人答案,像屈原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吧那就是他的答案他的世界,你可以不信,但也别小看别人的答案,说到底,这事谁能知道?没准谁对谁错呢?就像说宗教之间你也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他人的信,更友好的态度是试图去了解,至少是广见闻吧。
王老师这《千岁寒》,还有那《致女儿书》,都跟他这人似的,开头有距离,实际到后边儿是一通俗易懂善解人意,有的人是给一开头唬住了,比如说《千岁寒》的开头,咱这儿不有本书吗,我没征得作者同意啊,说得不一定对,我给你念:“时——觉悟者释迦族的明珠湮灭物质形式回归能量圈两个五百公转儿后,第三个五百公转儿内。”——这是从释迦牟尼之死说起,他是释迦族王子又是觉悟了的人可以算他们族的明珠了吧,明珠湮灭就是佛死了也叫涅磐,那自然是组成人的物质形式转化了而能量守恒,王朔可能认为涅磐类似于回归宇宙的本质,用物理词儿说他大概认为一切的本质就是能量,地球绕太阳五百个公转就是五百年吧,是指释迦牟尼死了一千多年后,就是禅宗六祖惠能出现的年头,“时”也是《六祖坛经》的第一个字。
他这样开头其实有种明珠、宇宙、太阳系的画面感,我老觉得王老师老编电影拍电影,所以开头有种电影感,还挺恢宏的一开头,不信你看下一句“大——欧亚陆架中央隆起雪山发源之水越撇越长撇出一江一河流入太平洋,流域地区是唐朝——女士主政时代。”——你瞧,画面移到中国唐朝武则天时代,而且从青藏高原流出长江黄河正是撇成一个“大”字形。所以你再往下看,“师——我该挎弓没挎弓挎着麻绳和柴刀,一顶头笠,一手提拳一手下垂”——这不是又对“师”这个字做笔划象形联想吗?把这个字部首拆开,左半边一竖一撇就是“麻绳和柴刀”,右半边的形状正是“一顶斗笠,一手提拳一手下垂”……以下依此类推。我喜欢这个文字游戏,而且每段头一个字竖着念就正是《六祖坛经》的头几个字,这让我想起古人游戏笔墨的趣味,但又是新的解码。
我知道我挺没羞没臊的,是挺傻帽儿,一知半解还冒充导读呢,谁都知道的事我还假装人不知道再给说一遍,是嫌多余。其实是因为前阵子周围老有朋友跟我说这书从开头就看不懂,我等于在这儿跟这些朋友交流一下,等于小范围分享点读后感。
你像王朔现在的书,《千岁寒》、《致女儿书》都显得前后不一,体例混乱,甚至感觉把这年那年没写完的东西都堆一块了,几年前写的东西里头还夹杂着今年新写的评注,这是要干什么?破罐破摔吗?反正没有妨碍我一段段看下去,我也没理会,他这么干成不成我也没资格评价,要说就是外行话了,我联想起一画家老师曾经给我讲过,大概意思是说有个叫塞尚的画家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他的有些画往往是一条线没勾准,就再在旁边勾描,最后就把一条条修改的痕迹留在完成的画上,有的画甚至就像未完成,等于是留下了绘画进行中的主客观状态在画布上。王朔也说要把修改的痕迹留在书上,未完成就未完成在那里,不了了之。但文跟画是不是一个理儿,我就说不来了。
还有所谓幻觉和妄想,庄子就在怀疑是蝴蝶梦见我了还是我梦见蝴蝶了,近年的大脑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看到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跟大脑本身的设置有关,是真是幻,至少可以存疑,本来就是个哲学命题。即便就是幻觉,文学不一直在写幻觉吗,我们觉得是瞎感觉,可在艺术家眼里也许是很真实的,我举个不太合适的例子,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本来是他一个人喝酒,月光一照,成三人行了,你说是幻觉其实都是他一人的影子,可确实他看见是仨人一块喝了。
大众文艺还有个你这幻觉跟大多数的感觉能不能相通的问题,可要是个人写作,没问题,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本来除了某几个特定的时间地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但少数人的事也为人类多元文化添砖加瓦啊,也反映精神探索之一端啊,只要不强迫别人接受都没问题。过去说魏晋玄谈误国,我觉得反倒是现在人人都那么实用,没什么人琢磨终极问题,有点缺乏精神高度,我自认为是很实用主义很势利眼的人了,可环境比我还实用还势利眼,那么多人没信仰,你信仰什么,钱吗?成功吗?我不是说该信仰什么,而是希望自己寻找答案,王朔对不对两说着,他至少是不甘心稀里糊涂接受别人从小灌输给他的答案,而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确实有多次被蒙骗的铁证。
- 玛花纤体新书解读最美“美人娇” 2010-08-18 14:17
- 波涛"胸"涌的性感诱惑 2010-08-18 13:31
- 性感潮女自曝甜美萌照 2010-08-18 11:33
- 依力:清纯嫩模时尚另类性感(组图) 2010-08-18 11:20
- 组图:向舒淇学习 性感魅力由心而发 2010-08-18 10:46
- 清纯嫩模的另类性感(组图) 2010-08-17 18:45
- 脸部按摩教程 30+MM照样能做弹性美人(组图) 2010-08-17 17:20
- 迷倒众生 6款夏日风情秀发性感魅惑(组图) 2010-08-17 17:20
- 舒淇泳装辣照慵懒性感 撑伞搞怪清凉无限(图) 2010-08-17 17:03
- 小张雨绮的性感大片 2010-08-17 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