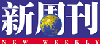作者的原意只有作者知道
《新周刊》:你会把《致女儿书》,视为王朔的忏悔录么?如果不是,那是什么?读《致女儿书》,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封总的感受是觉得自己肮脏。怎么看待一个男人把女儿作为告解对象去倾诉的这种心理?一个男人最后发现自己爱或者信任的女人,只有女儿,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
窦文涛:作者的原意只有作者知道,读者看书,翻开往往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各人自己而已,所以我肯定是以己度人有误读。封新城看完觉得他肮脏了,因为他也有女儿,我没女儿,所以说理解也是假的。王朔在书里明说,他的一生很明确,为自己,可这态度唯一绕不过去的是由己所出的女儿,在女儿面前他无地自容的心都有。他小时候跟父母似乎比较陌生,他觉得中国人的孝有问题,因为他从亲身经验认定父母在女儿身上得到的快乐早就抵消了他们的付出,再要求孩子长大了孝养父母没道理,而且他认为赡养老人该是国家义务,这一条在将来老龄化社会里独生子女可能要赡养多位老人的压力下是个思考。
我同意我如果有孩子,我本人老年要自寻归依不劳烦孩子,最好各走各路,但我的父母我总是骂自己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太少,大概因为我父母一辈子就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一切吧。
我记忆里他们算是宠孩子的,也可能天性有点软弱,对自己的正确性缺乏信心,爱犹豫,在管孩子方面就常常心软,打孩子总是下不去手。我们家在石家庄是外来户,独门独户,极少走亲戚,跟外人几乎没来往,一家人都比较自闭,父母年轻时吵吵闹闹过一阵,但现在家里人挺亲的,想起父母兄弟总还是温暖亲情。
记得我爸到晚年还老提起小时候打过我哥哥一次,我哥都忘了,可我爸为这事后悔了几十年,所以还是什么家庭什么孩子吧。可我不明白的是想起父母为什么总会辛酸难过,这感情里怎么有那么深的痛苦,是对父母为孩子艰辛一生现在一天天衰老的哀伤吗?不清楚,所以有时候我反而瞎想,将来跟我的孩子感情淡一些才好,算了我这没孩子的聊这个实在不靠谱。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写的时候坚定只冲着一个人说,冲着女儿说,其实是对自己的写作心态要求近乎苛刻,文学上评价我外行,可这至少是真心文字,拷问自我的文字。我现在也开始自己写了,有空就写。这有几个由头,一是有段时间简直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当然不是忧郁症,我离疯也还远,可得解决这问题,于是先看到王朔书里说他写作也是心理治疗,就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而且我也想王老师那么会说话,会不会跟写东西特别是口语写作的训练有关系?我是不是也得动动笔?同时又看到台湾一个姓侯的艺术家一本小册子,照片上感觉这侯艺术家好像把自个儿饿成灾民了,他真是把自己关起来写,从这儿才知道台湾现有种“自动书写”运动,还有几条原则,大概就是不要有任何杂念,不要有任何要写美文的概念,根本就不要想,脑海里出现什么就当即记下什么。
于是我也开始了,是管点儿用,写一通心里能好点,后来也不一定,但挺愿意写,我还不像王老师他可能还免不了有点估摸着早晚得见人的意识,我是纯粹就为自己我也不出书,那是完全诚实。我看了看内容,即便真要给人看那也得等我死了,等我所有认识的人都死光了才行,那也不行,有的人还要死后声誉呢你也不能给人拆台吧。诚实也难,当你在这过程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诚实也不是你能把握的,静看自己的心才明白心乱如麻,一条道有八个岔你往哪儿去,无数念头纷至沓来,你又不能同时写八件事儿。其实我最近正想问问作家王老师这事怎么办呢,哎就看见他这《致女儿书》,原来他早就这么写了而居然也遇到同样问题,甚至有些话都一样,比如“今天情绪太灰了,不想写了”等等。
所谓这种自我自动书写,或者叫无意识下意识书写,应该不新鲜,凯鲁亚克《在路上》算不算呢?这也是一种写作路子,我写是自己玩,人作家经验、表达比咱高一筹,那流出来的东西也许真有价值。我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文字表达方式,以前写东西吭吭哧哧总是太费力,因为对文章太有概念太有要求,象王老师他给我的启发是用自己的口语写作,结果这么一写真顺畅,也不假模假式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而且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打那儿起我写什么都像在沉默中一个人聊天。这不知道好不好,我也不是文学家,就只觉着合适我挺舒服的这么写。几年前记得我请教过文学家阿城,说胡适不是白话文吗,那我要这么写不就是明白如话吗?阿老当时说这不够,落在文字上还是得收拾,可我既然不给人看也就懒得收拾了。
《新周刊》:王朔一直是个争议人物,你觉得世人对王朔的种种看法(比如说痞子和疯狗和炒作)缘于哪些因素?
窦文涛:其实你发现没有,在今天社会,疯可以获得某种自由,不用那么压抑,有时候我也想当疯子,去那儿发现来晚了,座儿早都给人占了,还排长队呢,我想那我就当傻子吧,也接近本色,没人跟我争(笑)。王朔这新书里好象还提到,真疯了就是不能适应社会了,他自己现在还能应付。我跟王老师来往不多,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想炒作,可我倒是注意到他经常说他至少知道什么叫寒碜,我一度没明白他指什么,没准儿在有些人看来,他所谓的疯样才叫寒碜呢。
后来想想有点明白了,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寒碜不寒碜,你也有,拧巴就拧巴在这儿,比如说我是电视台主持人,台里要播我的宣传片,宣传词自然是夸我们自己的,夸我是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其实还是你们《新周刊》给的一奖,就象广告似的一天滚动播好几遍,可我一看见就觉得丢人,哪有这么吹自己的,最佳?我是吗?包括做广告这事我也是又想又不想,想是想钱,不想就是怕寒碜,别人做都挺好,到自己就老觉得我这德性上广告好丑,怕朋友笑话。
你想不到像我这样在节目里没皮没脸的人在这事儿上倒腼腆,还有让我走红地毯也寒碜,实际现在这都很正常,做了也没人笑话你,就是你自己太把自己当人了,可问题是游戏规则变了,这年头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事寒碜,大家都不觉得寒碜,观众也没意见,没准在别人眼里就你这样什么都不乐意才最寒碜呢,为谁拒绝为谁扛?到最后似乎只是拗不过自己。
再比如我作为主持人在各地一些场合经常需要说那些大话雅词儿,可我一说就脸红,为什么?反而当众说我好色我不脸红,那至少是真话,可要说我们胸怀天下,我就不自然,不是这话不对,而是我觉得自己都还没达到,人格修养上实在还没到那个境界,从我嘴里说出来这些词儿我就觉得寒碜,我自己没那么高我干吗要说那么高,当然可以说何必较真呢?把自己当工具当喉舌,说这些话不就是职业行为嘛。可你要把自己当成个说真话的人,就有个口是心非的问题,但谁会要求主持人说到做到呢?钻牛角尖了吧。重新洗牌的时代,你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的方针办?你是弄潮儿?还是老顽固?这种情况下,没准儿像过去那种男孩子会爆发叛逆心理,就觉得假善比真恶更讨厌,没那么好让我装那么好,更寒碜,还不如装恶呢,以恶制恶,我这说痛快了,可说谁呢,说我自己呢吧(笑)。
《新周刊》:你也是电视上的侃爷,在广东电台侃了7年,在凤凰卫视侃了11年。偶尔,会不会侃得有无力感和空虚感(或虚脱感),如王朔在纸上的多年失语?
窦文涛:你是说江郎才尽吧,我算窦娥泪尽(笑)。我当然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啦,才尽还是好听的,好像你原来还有过才似的,我觉得过去见识短还可以原谅,现在学习多了,要再认为自己以前那点东西叫才那就真有点不嫌寒碜了。这些年来我被电视大工业毁得不轻,现在正在恢复元气。其实我喜欢做少而精的节目,对我来说一个精品胜过百个粗制滥造,可电视台对产量需求太大了。我长期做两个节目,一周六天六集,还都以我说为主,我对我说话质量不满意,可要讲数量,估计是说话最多的主持人了,自己都觉得可笑,我得是多大一话痨啊(笑),所以我给组里人打气,咱是薄积厚发以量取胜,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王朔还可以搁笔多年,我一天也不能停,我太想休休长假充充电了,可除非把节目停掉,要不然我的节目连个替班的都没有。
我常常惋惜这个节目本来能做得更好,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这些人平常老看电影、艺术作品,有那个美感在心里,却忘了电视节目的制作规律,跟那些门类相比电视节目算快餐,尤其是目前中国电视业还是在求多快好省的初级阶段,象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象大姑娘绣花那么细致那么从容不迫。我们家人的性子都是慢工出细活,那天我翻出中学日记,还看见我把哥哥告诉我的一句话当成了座右铭:“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象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还“永志不忘”呢,可现在艺术品都得改工业品。过去我有个毛病,要做就让我认认真真做,要不我就不做,现在也不得不妥协。
这么说你可能有点不理解,比如说《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这俩节目都是我们原创的节目,不是说原创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最早的时候这两个节目幕前后都是我一个人为主,锵锵是即兴聊天,主持人的话题源于生活,那我就该多生活多看闲书多积累,可后来又有了拍案,这节目我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剪,干两天两夜,这还生什么活呀。我不能背稿吧,背稿就像抄一篇文章,可我的劳动就像自己写一篇文章,可我的节目量却比那抄文章的量还大。
前两年有那么一阵儿,真到了除了工作就是睡觉还睡不着简直了无生趣的地步,当时我冲着启明星发毒誓:谁也别想剥夺我的人生,谁也别想把我逼成精神病,再也不能这样活(笑)。领导也重视啊,可节目量不能减,就说找两组人帮你,你不用从头盯到尾,只管主持就行,可能这样肢解了我也好,手工作坊必须进入工业分工,要不累疯了,但伴随而来的是那种一个人的作品感我失去了,而且现在也只能抽出一半身实际还得幕前幕后紧忙乎。讲这故事是想看看这算不算现代大工业对个人劳动产生异化作用的一个案例。该怎么衡量价值呢?如果现在让我回到自编自导自演自剪一周只做一集〈拍案〉节目,我有把握让这个节目不但高收视而且成全台甚至全国精品,但是对电视台来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让我一周卖六集出来。当然我个人怎么着都行,现在也已经初步找到了平衡,可以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了(笑)。
《新周刊》:王朔说他一直在演名叫王朔的那个人。你是否有同感,也在演名叫窦文涛的那个人?若是,你演得累吗?你的解压之道是什么?独处么?你内心的是非与道德观念,和社会加给你的角色和公众形象,有着怎样的不同?
窦文涛:最早做《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是1998年,那两年我是轻松快乐的,因为那时候也怪,脑子里没观众,我人在香港,凤凰刚开台不久也没现在这么大影响,跟大陆观众挺隔膜,也没网站,更没有收视率这些东西,大概寄信也挺贵的,观众来信我记得都不多,我只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想说什么说什么,都是自己生活里的事,后来居然讲起黄段子来,到现在还有人叫我“天下第一黄”,不是因为我讲得好,只是因为我讲得早,当时并不是胆儿大,从这事你就可知我当时几乎没意识到观众的反应,可以说一点社会责任感也没有,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幼稚得可笑。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杂志评我是“生活和工作如一的人”,因为我的节目就是讲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连准备都不用怎么准备。后来大概一两年后,领导让我意识到了观众的存在,我感觉从那时起我的“劳改”就开始了,就是在劳动中不断发现自己的偏差,不断自我改造。
后来,也可能是个人经验讲得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又有人告诉我不应该老陶醉在个人小天地里,要关心社会关心大众,咱是听劝的人,一听人家说得对呀,虽然有点勉强但也开始聊忧国忧民,一试,真还挺火,就更上道了,直到最后人家称我为“社会良知”把我吓着了。再后来又有了收视率排名,我投入在工作上的精力以一年翻一倍的速度递增。我心里也渐渐有种感觉,劳改刑期在延长,似乎有期改无期了。
我说劳改是个玩笑,主要是学习尽量对我原来不感兴趣的事感兴趣,其实我的劳改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些年也算做出不少观众们认可的节目。可凤凰是个挺有理想的电视台,要求胸怀天下关心公共事务,我的格局跟这个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有时候想做播音员挺好,虽然人说我报新闻不可信,可照本宣科毕竟不大涉及到人的内在思想感情,即兴谈话节目就不同了,它需要真心实意表达自己,你心里没有,装出来的大家一眼就看穿了,所以说到底你要受欢迎就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急,人民就是大多数观众吧,那我的脉博本来没跟大多数跳在一起,能改造得跳在一起吗?还是上班的时候跳在一起,下班的时候不必跳在一起?我是不是太苛求诚实了?过去我觉得我在电视上比在生活里还诚实,当然虚伪的时候也多,而现在我已经慢慢能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两回事了。
但有件事我一直较真,觉得《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一定要“我口说我心”,甭管下了班怎样,录像的时候我得调动全部注意力,让自己变成那个人,对这话题充满热心的那个人,我觉得只要我心里没到那儿嘴上就不能说到那儿,要不你就是玩假的,聊天的生命就在真心真话,这样问题来了,你怎么能保证一年三百多天天天都能跟观众心连心呢?那听上去也是一种很恐怖的现象。不是说佛心就是众生心吗,我有时幻想要修到佛心那就跟每个观众包括他们家里的猫狗都悉知悉见啦(笑),这幻想反映至少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为做好主持人不惜改造灵魂的事。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我私人喜好的事大部分人不一定关心,即兴聊天这种形式又很难避开自我流露。你可以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可你逃不出规律,电视台的规律:抓住大家关心的话题就多人看,只说自己想说的,观众就像你身边的朋友一样少,你说少我也不在乎,多元文化嘛,联合国都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呢,不能保护一下我吗,可收视率不保护你,广告商不保护你,电视台说这是社会公器,我们的责任不是保护你,而是你有责任去为天下苍生鼓与呼,我们还希望你发出声音保护更多更需要保护的人呢!
谁说的都在理啊,我这么讲理的人咋能不接受呢,所以转头回来还是问自己,为什么人民关心的我不关心呢?不行,我太自我干脆说自私吧,得改造自己,改造到灵魂深处,我真的试了,现在还在试,费了老大劲,效果不显著,胸怀天下这事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也许我这种凡夫俗子只配给胸怀天下的人当工具,帮他们实现包打天下的理想吧,说是帮,其实是图人家给你那点盘缠,好让你在帮人之外,能继续走你自己那条独木桥。
我有时候汗流浃背正改造的时候,也会猛转一念头:我会不会入错行了?男怕入错行,女的就怕嫁错郎,可能本来有些事就该某些人去做吧,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龙生九种人生亿万种,有人天生就是忧国忧民的,人民有他们整天惦记着呢,就连他们都是分派的,有忧一国的有忧一村的还有忧地球的,互相间也常有矛盾,我还知道有人天生就是画画的,有人天生就是体验生活写小说的,甚至有人天生就是品吃品喝潇洒走一回的,都算为人类做贡献,那我本来该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好像离了这行还真没饭吃,那我是不是本应该就是一职业主持人,少想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别人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只不过咱得尽量琢磨着把人需要我说的话说得漂亮点,底线别昧了良心就行,什么真的假的,这就一工作,空姐的微笑都是真的吗?舞蹈老师让女孩们上台表演要露八颗牙,那是真笑吗?是不是对工作认真就可以了,不必要较真吧。——不行不行,你怎么能跟空姐、舞蹈队的妹妹们比呢,人家不笑都比你好看多了,你得高标准严要求,你的专业就是为观众服好务,老板不是说专业主义激情吗?在台上你必须真心笑,必须把不认识的观众当亲人,这是你的专业情感,真听真看真感觉。专业之外也没什么可拧巴的,你不是说人就是分裂的吗?矛盾理所当然,像多棱镜多个面向组成一个你,像最硬的钻石每个面向都透明都从心出发——你看,我最后绕明白了,可是真明白了吗?
我没什么价值,我唯一的价值就是假如有人居然那么稀有,从头到尾看了近十年《锵锵三人行》,那他就等于旁观了一个超长版真人秀,讲一个涉世不深无知无畏的小混混意外跳进电视里,而后在公众监督下,被一步步社会化成人化的过程,这过程现在还在天天进行,而我总觉得没走好,走得不顺,但似乎我们的老板还是对我寄予期望,给我宽容,希望我走下去,那我就再走走看,我从来不能见好就收,就像恋爱一定要搞到无法收拾还没完没了,其实你别以为我发愁,就是这么一犹犹豫豫的性格,我还能欣赏自己这场秀。
《新周刊》:“三人行”在中国电视界延伸出了一类脱口秀效仿者,基本上没有侃得过《锵锵三人行》的影响力的。除了电视平台的原因,你觉得是因为他们的主持人太世故还是不够世故?太主旋律还是太不真诚?或别的原因?
窦文涛:很抱歉,我没看过,基本上我的电视当监视器用,有时看看新闻、看看纪录片频道,据说许多做电视的都不看电视。我是头驴,一向只会低头拉磨,不懂抬头看路,全心全意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而后逃离工作。业余时间看电视怕又会联想起工作,那就又摆脱不了了,平衡又破坏了。我体会人必须别有洞天,拥有一个自己玩的世界,我在里头干什么你别管(笑),但这个世界重要过一切,也终会是一切的源泉,外面世界整天风起云涌,可你心里这块儿千万别失守。
《新周刊》:你的F40心态如何?新周刊做了一期《F40:新中年肖像》: 你在历史上从未见过这样一代人——生命的一半是暗,另一半是明;一半是凝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革命的尾声,另一半是开放的先声;一半是被压抑的服从,另一半是被推举的先锋;一半是诗意,另一半是商业;一半是根深蒂固的坚持,另一半是后来居上的放纵;一半是积聚财富的市场掘金客,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这一代人就是F40。 你今年正式40岁,你的F40心态如何?你觉得你跟大多数F40一样吗?
窦文涛:不知道大多数,40岁一到,我这头驴好像也摘了眼罩试着抬头看看路了。我最近明白的事是我这四十年都是随波逐流的四十年,太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四十年,许多事一开头自己的感觉就是对的,但也没坚持结果倒听了别人的,所以要听别人的,但主意得自个儿拿。看周围人,每个人都在做他要做的事,有人求名,有人求钱,有人求权,有人求官,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上进步着,你不能看别人要什么你也去跟着要点什么,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我要做的事呢?做我要做的事,这对我现在最靠谱。
- 视频:《时尚装苑》明星走红毯,有苦说不出 2010-08-16 10:51
- 视频:《骇时尚》56期 失恋接拍全裸广告 LV设计师的“... 2010-08-13 15:58
- 视频:《骇时尚》54期 这是一幅会引发“车祸”的户外广告 2010-08-11 11:55
- 乌克兰艺术家用胶带作画贴出电影中场景(组图) 2010-08-11 11:18
- 美国艺术家在结冰湖面上创作巨型几何画作(组图) 2010-08-10 10:52
- 视频:《第一时尚》中国男模集体走红 2010-08-06 14:58
- 视频:《骇时尚》51期 全球第一只手机广告 2010-08-06 10:48
- 视频:维多利亚的秘密2010年电视广告 2010-08-05 18:12
- 陈文茜:像艺术家一样穿 像政治家一样活 2010-08-05 13:15
- 黄晓明与baby恋情疑为炒作 正牌女友被曝光 2010-08-04 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