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云(新浪网友) 图/赵婷 欢迎网友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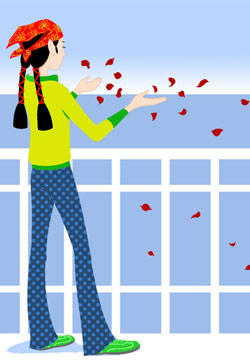
对于花草,我绝对是个外行。这个遗憾应该归咎于我出生的那个小镇。
小镇三面环山,山上觅不到水也寻不见树,一眼望去就像一个驼背的老人披了件斑驳淋漓的土黄色的外罩。这里的生灵除了牛羊,没有不抱怨天气的,一年十二个月,三个月骄阳似火五个月冰天雪地,剩下四个月既无骄阳也无冰雪但要忍受从日出吹到日落的风沙。可以想象那样挑剔而娇贵的花儿如何有力量抵御这种致命的摧残?所以在小镇上任何时候你都不能随心所欲的看到花儿,花儿们用拒绝生存的方式表示了对小镇自然环境的厌恶。当然,如果执意要寻个究竟,可以去偷视为数不多的爱花人家的院子,隔着墙就能看到星星点点的花瓣儿,全是耐旱耐寒的芨芨草、太阳花、玻璃翠、仙人掌之类的,幸运一点可以看到月季,但都是一副楚楚可怜、奄奄一息的模样。所以至今我也识不得几种花,更不要说关于什么花儿喜荫什么花儿喜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怠慢她们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但凡人对某一物件不感兴趣,大多源于两种可能,一种是尝试过,觉得无趣;一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想当然的认为无趣。我与花儿的趣与无趣应该属于后一种。所以,很长时间,花儿于我也好,我于花儿也罢,都是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彼此遥遥相望。
后来到省城读书,虽然那里的气候也是干燥而寒冷,但交通便利,讲究市容市貌,城里人亦有闲情和条件摆花弄草,所以温暖的季节,特别是节日里,到新城区闲逛,随时都可以观赏到南方的奇花异草,在人工设施的精心保护下争奇斗艳。虽有造作之闲,但毕竟让在我如花儿的年纪知道了什么是花儿。
入学军训的那阵儿,班上有个女生得了急性阑尾炎,做了一个痛苦的手术,孤零零的躺在病床上。全班女生彼此还不太熟悉但为了表示友谊和关心,私下里编了几个小组去医院陪床,还慷慨的凑了钱买给她一大束鲜花和一堆营养品。花儿是我和几个女伴一起买的,那是我第一次进花店,当淡雅的花香扑鼻而入的一瞬间,我竟莫名其妙的产生了错觉——进了百花仙子的后花园。同伴们唧唧喳喳很内行的开始选花儿,我一句话都插不上,只能溜达着看,瞧见一朵儿感叹一群,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一种自己熟悉的花儿——邻居张大娘养过的月季。当时我真的有点欣喜若狂,抽出一枝红色的急切的建议她们:“为什么不放上一枝月季花呢?”大家一愣,刷的把头转过来,看着我手里的花,哄堂大笑,有一个竟笑出眼泪来了。“那是玫瑰,我的大小姐。”“你没见过玫瑰吗?”顿时,我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我窘极了,去问老板娘,看得出她也是强忍着嘲弄的神情,躲闪着眼神对我说:“玫瑰和月季是很像,但我的店儿里从来就没卖过月季花儿。”我拿着花站了好长时间,直到女孩儿们付了帐若无其事的叫我一起走。晚上我忍不住藏在被窝里哭了一场。我为那枝让我丢尽面子的玫瑰憋闷了很长时间,好像一千个理由都无法释解自己的见识狭隘和尴尬。从那以后玫瑰成了我记忆中唯一有故事的花儿。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自作主张的跑到青岛谋生,刚刚毕业一身的豪气,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以为背上剑就是侠客,拿了枪就能打猎。殊不知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离真正的生活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一个月下来,青岛市里的大街小巷风景名胜我走遍了,也看遍了,工作却连个影都没有,兜里的钱一天比一天薄,人也开始消瘦下来。终于在那天坐在马路牙儿上啃完一个老玉米之后,决定去青岛的经济开发区黄岛碰碰运气。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我觉得自己真是大幸之人,先是在黄岛人才市场碰到了一位热情好心的老乡唐红亚,于是第一天就有了暂时落脚的地方,接着又在短短一周,找到了工作——是饥不择食的那种,一天十个小时坐在那儿为一家私营的只有十个人的小广告公司做简单的设计和排版工作,尽管如此,那会儿觉得自己是“某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找到工作后我从唐红亚那里搬了出来,和公司里正在找房的两个女孩,徐丽、素兰,合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虽然四壁皆空,但一想到不必坐在马路上啃馒头喝凉水,心里宽慰了许多,关于忆苦思甜的理论我是在那时学会运用于实践的。徐丽和素兰只有十八九岁,比我小得多,家在农村,读完初中,就来到这里讨生活了,我问过她们这麽小就出来,父母放心吗?她们说,既然他们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那只好自己出来找了。我琢磨了好久,也没弄明白,哪有父母不让女儿过好日子的。
经理是个黑心而苛刻的人,从来没有按时发过工资,即使发了,也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扣上几十块钱。当时的处境只能是生存高于一切,包括放弃向老板讨回公道的权利。三人不约而同的想到减轻房租负担,决定再找一个合租人。人不难找,很快素兰的同学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女孩子,隔了好几层,彼此一点都不了解,但我们关心的是谁来帮忙分担房租,而不是对人挑三拣四,就把这个问题轻易的忽略过去了。
如果老板不扣我们的钱,如果合租人不是林小娜,我想,青岛在我心中永远如我当初对她无限向往时的湛蓝和博大。但一切都在林小娜搬进我们原本清静和暖的小家之后,失去了平衡。
林小娜与素兰、徐丽同龄,来自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她说她不想像她爸妈一样一辈子打渔为生,半年前不顾父母的反对跟着一个见过世面的老乡来到了青岛,用她的话说:想活出个滋味。林小娜是我见到过的比较典型的山东女孩,身材高大而均匀,肤色黝黑,有着海边女孩特有的常年被湿润的空气滋养的水嫩,性格开朗,一天到晚笑容满面,人缘也是极好的,搬进来的那天晚上热情的请我们三个严重缺浑少油的女同胞吃了一顿排骨炖土豆,那顿饭吃得我们既羞涩又解馋,我敢肯定,林小娜晚上做梦都在笑我们三人的难民相。最初的日子里我曾那样的倾羡于她的亲和力,以至于不自觉的在人面前模仿过她的微笑,因为这份欣赏,我和她走得很近,彼此关心的程度竟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了我和徐丽素兰的友谊。
我们忽略掉的问题终于还是摊在了桌面上。两周之后,林和我们开始不断产生摩擦,原因似乎很简单:其一,林好像不做什么工作却从没有为一日三餐发过愁,而且还有一些怪异的行为,比如我经常起夜时碰见她躲在洗手间里化妆,问她做什么,她总说去参加什么演出活动,我没法怀疑她的微笑,但她子夜演出的时间,让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其二,林有太多的朋友,而且是清一色的男性朋友,常常出其不意的来串门,明显的影响到我们三人的休息,甚至于自由的生活空间。关于这些不能避免的小矛盾,素兰曾经和颜悦色的找林小娜谈过,结果总是好一天坏三天。遗憾的是我们三个都是习惯于感恩的人,想撕破脸皮时总是不约而同的记起那顿排骨炖土豆。
有的矛盾可以隐藏一万年,但我们的矛盾已经酝酿成了一座活火山,不可抑制的迸发了。那天,徐丽和素兰上午去跑业务,结果不尽人意,被老板痛骂了一顿,害得她们躲在卫生间哭了半天。中午的时候,两人垂头丧气的回到家,本想好好睡一觉,没想到林小娜带着四五个人在家乌烟瘴气的聚餐。从衣着和言谈举止上就可以看出她这些朋友的来路,不是绿林好汉就是土匪,但绿林好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素兰的脾气比较急躁,郁积了许久的怨气很快被满屋肆无忌惮的说笑声燃了起来。她趁我和徐丽坐在床边叹气的功夫,把林小娜从屋里低声吼了出去,很不客气的让她把朋友轰走。林小娜不吃素兰这一套,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在门外低声争吵起来。我赶紧跑出去,想制止素兰,怕把事情闹大,以后不好相处。但推开虚掩的房门的那一刻我吓得倒退了两步:林小娜和素兰狠命的撕扯住对方的头发,咬着牙在那儿僵持着,没有一点声音。我感到自己的手在抖,但还是胆战心惊的过去拉她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两人扯开,正暗自庆幸,没想到素兰抡起胳膊“啪”打了林小娜一记耳光,林小娜被打怔了,但飞快的还了她一个。两人满脸通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的粗糙黯淡,泪水在她们的眼眶里随着脸上抽搐的肌肉激烈的抖动着,但没有流下了。周围的空气凝固了,憋得我喘不过气。“我不干净?你又是什么东西,别以为你暗地里做的那些勾当没人知道?让我滚,做你的白日梦去吧!”林小娜以极其恶毒的口气抛下这句话,转身进了屋,顿时她的房间响起了一片放肆而高亢的笑声。我不知道林小娜和素兰刚才在说什么,但从素兰茫然的眼神和面无表情的神态上猜测,她们之间有着无人知晓的秘密,至少是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有点晕。素兰下午没去上班,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搬走了,除了门钥匙连张纸都没留下。三天之后,徐丽也搬走了,说同学在淄博给她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她要赶去上班,当然是借口。
素兰的不辞而别,徐丽的奔赴前程,换来了暂时的安静。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感到恐慌。我不相信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大事,在我所有可以发掘的理解中,十八岁的女孩应该是点缀校园的鲜艳的花儿,飘在天空中纯洁的云啊!但一想起她们吵架的情景,内心深处又不敢完全否认某种可能。我被这种反反复复的肯定和否定折磨得筋疲力尽,决定一走了之。令我懊恼的是,在发下个月工资之前我没办法走——兜里只剩十元钱,而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有四天。我心里盘算着这件事,没心思去理会林小娜的任何什么事。
那天早上,林小娜出人意料的在我上班之前起了床。我忙着洗漱,没注意她与平日里有什么不同。正准备出门,她在背后叫住我:“艳姐,今天我过19岁生日,如果你晚上没事就早点回来一起吃饭吧!”她竟然穿了一身玫瑰红的运动衫,站在那儿热切的等着我的回答。我答应了,说实话我无法拒绝的是她那身引发我无限好感的运动衫。
晚上又超时工作,下班的时候,饥肠辘辘,迫不及待的想到了吃,才猛的记起答应林小娜回去吃饭的事。我有些为难:19岁是女孩子最美的季节,不管林小娜是不是亵渎了她的神圣,但她父母给予她的这段生命没有错。应该买点东西表示祝福,但10元钱能买什么呢?深秋的海港,风刮得格外的凉,我沿着亮起路灯的大街慢慢的往回走,手被冻得不听使唤了。路旁的店铺播放着嘈杂的歌曲招揽生意,我漫无目的的在这些污七八糟的音乐中闲逛,想为十块钱碰碰运气,竟不知不觉走到一家鲜花店,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推开了门。我没看花,站在门口问老板娘:“有没有红玫瑰?”“有啊,有啊,你要多少?”“多少钱一枝?”“四元。”“太贵了。”“姑娘,这已经很便宜了,刚从云南空运过来,新鲜得很。不信你过来看,还没打开包装呢。”我站着没动,心里紧张的盘算着:十元减去四元,剩下的六元钱怎么花才能坚持三天。老板娘已经拿了五六枝举在我面前让我看,花儿含苞欲放,凝重而鲜亮的红色在寒气里显得异常的温暖。“买一枝。”别无选择,我只能买一枝。
出乎我的意料,家里只有林小娜和三个女孩子,围坐在桌前,刚刚把蛋糕切好。看见我,林小娜惊喜的叫了一声:“我以为你有事。”“生日快乐!”我托起她的手把玫瑰放在了手掌心。整个晚上,林小娜都异常的激动,眼睛一直明亮而潮湿,她逼着我吃掉了最大的一块蛋糕,她说,她想借我的勇气用一用,蛋糕代表她的诚意。我以为只是开玩笑的理由罢了。后来女孩们走了,我和林小娜点着最后两支蜡烛,静静的坐在桌旁说话,确切一点儿,是她在倾诉,桌上的玫瑰一直在用真诚和关爱抚慰着林小娜19岁的心灵,我想是那样的。
“这么久,不知道素兰怎么样了。艳姐,素兰到‘梦之行夜总会’找过工作,这事儿可能只有我知道。那天晚上我去夜总会找朋友办事,碰巧看见素兰和一个老头在跳舞,我挺奇怪,她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就偷偷去问老板,他说,素兰是来找工作的,正在实习。我特吃惊。两天后我又打电话问她的情况,老板气哼哼的说,她脾气不好,把她辞掉了。实际像我们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没有多少文化,还想一口吃个胖子,羡慕人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懒得奋斗啊,拼搏什么的,所以一旦遇到困难,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很容易走上这条路,素兰肯定有她的难处,我没有关心她,反而当着你的面羞辱她,谁受得了?唉,后悔也没用,如果碰到她,我会道歉的。艳姐,说心里话,今天我特别怀念在家和父母一起出海打渔的日子,真的!”她垂下眼帘去看蜡烛,沉浸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段美好回忆中。“小娜,你看这枝玫瑰,多美,实际,你和这枝玫瑰一样美丽而年轻,只要好好珍惜,一切都来得及。”我清楚的记得她听完我的话眼睛突然间变得清澈见底,烛光的映像在她瞳仁里欢快的跳跃了一下。晚上我一直在胡思乱想林小娜的话,头疼得要炸开一样,吃了三片去痛片也没管用。
我终于度日如年的把可怕的三天挺过去了,拿到工资那天,立刻就辞了职,准备第二天回青岛。因为打算一大早就走,所以想提前和林小娜打个招呼,顺便算一下水电费,等了很晚,还没见她。因为知道她有晚归的习惯,我就睡了。没想到睡到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是房东夫妇,还有一位满脸皱纹眼睛里布满血丝的老人,奇怪的是后面跟了三个警察。房东表情严肃的说了句对不起,领着人直奔林小娜的房间。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夜未睡。第二天去房东家送水电费,没等我问,房东煞有介事的附在我耳边告诉我:林小娜死了,警察说和毒品有关,好像她想和老乡带着钱一起逃走,被同伙发现了吧,警察抓了好多人!昨晚他父亲过来处理了后事,唉,什么世道!我明明记得那天的太阳又大又亮,可我跑在回去拿行李的路上,感觉自己瞎了,什么都看不见。我带走了那枝即将枯萎的玫瑰,在黄岛开往青岛的渡轮上我把花瓣撒进了轮船扬起的碧玉般的浪花里。我希望她在碧波里能够重生,可以像我一样自由的站着阳光下的轮船上,乘风破浪,笑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但我知道她永远的消失了,像一片儿受伤的浮云,禁不住半丝沉风。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没再以任何方式接近过玫瑰,好在丈夫也不是一个秉花谈情的人,无意间遂了我逃离那段记忆的心愿。
本来最能体现玫瑰价值的情人节在我的生活里一直是个其嗅如兰,不远不近,不惦记也不盼望的日子,丈夫也疏于这种浪漫,所以四年来我们没有特别的关注过她。没想到今年情人节,我却意外的收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枝玫瑰——丈夫冒着初春的寒风排了二十分钟的长队,花了比平时高出十倍的价钱买回来的。开始我挺奇怪丈夫这份出人意料的礼物,但当我领会了他真诚而充满爱意和鼓励的眼神的时候,我知道没必要去问为什么,玫瑰就是答案。手中的花儿是玫瑰中的极品,在丈夫浓浓深情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富有活力。我想,那世上绝无仅有的玫瑰红,一定是人的鲜血滴成的,否则她不会如此有魅力,让任何人看到她都会联想到爱情、友谊、惦念和关怀——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玫瑰把我带回了童年,带回了大学时代,带回了青岛,我倚在丈夫的怀里给他讲小镇,讲做手术的女同学,讲林小娜,还有那枝让我饿了三天肚子的玫瑰。我还告诉了他一个小小的心愿:我想用世界上最美丽最纯洁的玫瑰为所有在海边拾贝壳的小姑娘盖一间遮风挡雨的小屋。丈夫说,行啊,我来种玫瑰。
本文章及图片版权归新浪网与文章作者共同拥有。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