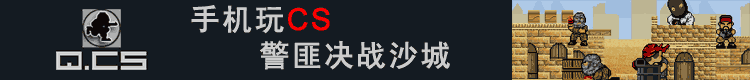文/林文杰
她想,她这朵百合怕是要凋零了。在这个连空气都逃脱不了爱情的夜晚,无力地盛开,黯然地枯萎。
情人节的前夕,她像朵恶之花,在摧残中凋零和破败。
她30岁,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海龟”,在巴黎被咖啡的浓香和精致的生活浸润了三年,开口便是极优雅的法语,和对法菜的如数家珍。本质上,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女人,三年里,以每天一封电子邮件,每周一个越洋长途的频率,和留守在上海的先生互诉衷肠。上海女人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异乡国度,都能游刃有余地操纵情感和生活,却是从来一个不拒绝诱惑,但也不和诱惑私奔的女人。相比之下,上海男人有时则脆弱得多。
举棋不定地往往是男人。
他的先生,就是在寂寞的三年里,因为忍受不了寂寞的滋味而越了雷池。回到上海,她知道了事情的全部,提出离婚。那时她已经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经常奔忙于欧洲和上海,致力于推广葡萄酒文化,并且准备出一本书,叫《舌尖的舞蹈》,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葡萄酒。她忙得天翻地覆,就想赶快把家里的事解决掉,以便无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她在工作中爱上了一个年轻英俊的波尔多男人,并在一次赴法的出差中,到男人的家族酒庄里作客,在绿草如茵的群山之中和酸涩甜蜜的红酒里度过了难忘的激情时光。
上海男人是善于在混乱之中摸出门道、理清思路,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的。此时,她先生的食品生意正做得如火如荼,仔细掂量,无论在应酬场面上,还是将来生意的前途上,她都是个优秀的无法取代的角色。于是,提出要和她重修旧好。
波尔多男人在上海开了酒吧,每天晚上,她都去那儿喝酒买醉,他在那里为她准备一支百合。他喃喃叫她“LILY”,像两个年轻的情侣,他们互相依偎含情脉脉。回到家里,她先生又对她万般宠爱,决不计较她的夜夜笙歌和身上其他男人的香味,就这样耗着,这边谁都没提出来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那边谁又都没提出来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结婚的事项。
转眼情人节要到了。她意外地发觉自己怀孕了。医生说“恭喜你,你要做妈妈”的时候,她疑惑了好半天,觉得这个人不是她,这件事应该和自己无关。她下周还要去北京做个推广会,下下周和出版社的人谈合约。
她把这消息告诉了先生,他正要出门,快速地转动着眼珠子,边拿大衣,边朝门口走,说,如果是我的,那就生下来吧。她告诉波尔多男人时,他正在酒吧里和朋友大谈和上海女人的艳事,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说,好啊,我要送一支花给你,恭喜你们啊。然后又继续喝酒。
情人节那天,她约了相熟的产科医生,一清早便到医院做了堕胎手术。因为身体虚弱,留在医院的临时床位上休息。坐在床上,她看到窗底下的鲜花铺子里店员忙得不可开交,把包扎好的玫瑰送走。街上的年轻人手中,多是拿着一捧捧各异的花束,一朵朵骄艳盛放。她想,她这朵百合怕是要凋零了。在这个连空气都逃脱不了爱情的夜晚,无力地盛开,黯然地枯萎。
出院的第二天,她就在外租了一个带花园的屋子,过上了独居生活。太阳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她经常在院子里晒太阳。
手术后遵从医嘱,她需要常常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