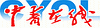中国式相亲如同交易:先讲家庭条件再谈收入
□焦虑的母亲告诉女儿要多参加相亲活动,在一个她还“值钱”的年龄。
□相亲对象从见面到确定关系的“忍耐时间”是三顿饭,“见了三次,你还对他没有明确表示,会觉得你好过分啊”。
□在相亲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结合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攥着印有“机关鹊桥联谊”字样的入场券,25岁的袁妮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集体相亲活动。
见面地点在一家拥有欧陆装修风格的四星级大酒店。入口处,站着两位穿着入时、烫卷发的“中年阿姨”,一望而去有种“事业单位的威严”。她们的任务是督促每位来宾填写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面的问题简单极了:哪里工作?有没有北京户口?月收入多少?
作为交换,袁妮可以从中年阿姨手里获得一个红底黄字的号码牌——将号码牌挂在胸前,才能进入相亲现场。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相亲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商业交易
袁妮坐在舞台下,打量着轮番上台的单身汉。按照规则,他们要先在舞台上走段“猫步”,虽然看上去更像是“几根柱子在眼前挪动”。大屏幕上不断变化的大头像与似乎永远不变的“硕士、有房、有车”等个人信息构成了某种稳定的结构。
在中国现代相亲市场里,袁妮只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中的一个。每一天都有单身男女在婚恋网站注册,而相亲机构中的翘楚甚至拥有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实力;一档相亲节目曾一跃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30余年来,市场经济重塑了这个国家的面貌,而相亲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拥有了某种商品的味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选择一只绩优股一样,人们热切地期望能够从市场中找到最好的那个人。
“爱情紧紧地同实用主义纠缠在一起”,米娜·伯里-坦森在上海生活了13年,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作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经讲起,“我经常在街上看到母女俩,听到她们的对话,‘他条件怎么样?有房子吗?有房贷吗?’”
一名今年26岁的女记者3年前刚到北京时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与相亲对象见面前,对方的父亲要求先见一见她。那是个洗浴中心的大厅,大叔穿着体面的西服,脚上却套着双蓝色拖鞋,露出里面大红色的袜子。
谈话开门见山,大叔毫不兜圈地问了买没买车、有没有北京户口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大叔继续追问。
“2000块。”为了结束这场“糟心”的对话,女记者给出了一个令大叔“糟心”的回答。
果然,相亲到此为止,大叔的儿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无论是在上海的人民公园或者北京的中山公园,都不难找到蜂拥而至的家长。他们捧着印有子女照片的征婚简历,在几百张并排的征婚海报前反复挑选,而每一张海报顶部所列明的条件或要求中,都会清楚地写明,判断合不合适的首要标准,往往是收入、财产或户口这样的外部条件。
《中国式离婚》的作者王海鸰曾经在她的微博上转述了一个焦虑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告诉她女儿多参加相亲活动,因为她还在一个“值钱”的年龄。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相亲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商业交易。”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中国式的相亲热潮。
一个报名参加了中国相亲节目的外国人的故事或可成为佐证。在节目现场,穿着紧身裤与条纹衬衫的主持人问他,喜欢哪种类型的姑娘。他在回答里小心翼翼地强调了独立的个性和文学品味。但在剪辑后的版本里,他的答案只剩下一句——“我喜欢丰满有曲线的女人”。
你已经是硕士了,得找博士了,博士怎么好找呢?
这场机关鹊桥联谊会有将近100人参加,但袁妮并没有打算从中带走一个如意郎君。她从英国硕士毕业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外表上看仍然像是个留着蘑菇头的大学生。当在体制内工作的叔婆郑重其事地把入场券交给她时,她只是觉得“搞笑”和“好玩儿”。
她甚至大咧咧地穿着T恤走进了相亲现场。然而,大堂里光亮得像镜子一样的大理石地面与会场里踩上去很有厚度的高级地毯都让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来自清华大学。”一位男士的自我介绍引来了一片“哇”声。另一位30岁左右的参与者则老练地调动着女同胞们上台表演的情绪:“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就不要有什么放不开的嘛。”
袁妮觉得尴尬不已。她拎起包,落荒而逃。
事实上,自打踏入社会,她就没少遭遇这样的尴尬。
“妮妮,你要赶紧找!你已经是硕士了,得找博士了,博士怎么好找呢?”在老家打来的长途电话里,外婆反复叮嘱。
她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个“优质银行男”,比袁妮大五六岁,在相亲领域颇为老练。一顿饭时间,他旁敲侧击地询问了袁妮在老家住城区还是乡下,平时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以及工作状况等问题。
“我有种被默默估价的感觉,特别不爽。”
而袁妮关心的问题恰恰相反,她想与对方分享关于旅行和读书的事情,但说起这些,“银行男”的回答大多只是“嘿嘿嘿”的笑。
在整顿饭局里,唯一令袁妮眼前一亮的瞬间是,“银行男”说自己一辈子都很顺利,读书成绩好,工作好,但有时候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是我唯一觉得他像是有个性的一句话。”袁妮回忆。
在她的单位里,同事刘畅的相亲经历更具有典型意义。她是名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从23岁算起,她已经有了将近3年的相亲史。
在刘畅的印象里,大部分相亲过程都大同小异:先讲家庭条件,再谈单位收入,如果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党员,也被当成重要的比较优势。“前三脚”踢开后,偶尔会有介绍者补充一句“人挺好的”或者“相貌如何”,结束语则是“他也多大多大了,挺着急结婚的。”
在刘畅看来,大部分时候,相亲对象从见面到确定关系的“忍耐时间”是三顿饭,“见了三次,你还对他没有明确表示,会觉得你好过分啊”。着急了,就发来短信,“我觉得你条件挺适合结婚的,行不行”?
“我特别受不了‘适合结婚’这个词,就像做拼图一样。你可以说不喜欢我对我没感觉,但什么叫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这是议价呢?”刘畅觉得,相亲这事儿被物化得“挺可怕”。
在相亲时代,她的坚持被很多人视作“异类”。见面前,她总会问介绍人“这人有意思吗?”“什么性格?”介绍人则会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这个不重要”。
“他们会反问我,什么叫好玩儿?什么叫有意思?”刘畅说。
这个相亲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刘畅的一个老同学,做生意发财成了小老板。他在交友网站办了一个白金卡,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女朋友。
白金卡还没过期,他扔给了一个被自己看做“屌丝”的男生,“你接着用吧”。
社会很多方面都让我们不安全,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张安全牌,如果想去真爱,成本太高了
几次相亲下来,袁妮觉得“胆战心惊”。但热心的叔婆仍然希望为小姑娘寻觅一个中意的对象。每回袁妮到家中做客,叔婆总要先摆上一盘水果,盘算盘算她的终身大事。
“做生意的你可能不喜欢,工程师你喜不喜欢啊?我觉得跟你最合适的,还是要去文化部找找。”叔婆对社会看得透彻,“做金融的也很好,可以考虑啊。哎呀不过现在做金融的都已经有对象了,人家现在的小姑娘啊,瞅得可准了”。
许多年前,人们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但是如今,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选择配偶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未来生活的质量。
“婚姻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资源的方式。”在一本研究中国“剩女现象”的书中,作者罗珊娜·雷克指出。这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相亲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结合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更确凿的佐证出现在《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近八成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适合谈恋爱;受访的90后大学生则大多持“无房不婚”的观点;而在理想相亲对象的选择中,“公务员”这一职业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不同的权力网络里,相亲模式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的王敏今年28岁,漂亮、聪明,仍是单身。她所在的单位曾经组织过一次联谊活动,对象来自同区公务员系统。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区的?至少得到北京市公务员系统吧。”
“为什么选择相亲这个通道?因为除了它是可见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堵住了。福利制度、高等教育给我们的保证太少了。社会很多方面都让我们不安全,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张安全牌,如果想去真爱,成本太高了。”王敏说。
但这个爱看话剧、喜欢读野夫的书的女孩仍然用力抵抗着现实,“婚姻是大路货,爱情才是奢侈品。”她说。
最近,又有一个条件出众的男孩子出现在王敏面前。坐在家里,她打开一本叫做《淘到个好老公》的书,那是妈妈送给她的礼物,翻开第一页,每个条件都能打对勾,翻到第二页,赫然写着“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吸引”。
“完了,这就是1和0的关系。”她哑然失笑。在好友圈的微信群里,她这样求助:“有感觉的有硬伤,没硬伤的没感觉,怎么办?”
“没爱情结什么婚?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群里一个好友这样回复,她在电视台做主持人,今年29岁,也是单身。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伴侣,但是她也知道“时间并不多了”。
“如果到30岁以后,我需要跟一个人结婚,他符合所有的条件,仅仅是我不够爱他。我想我仍然会跟他结婚。”她说。
最后,当被问到她还算不算是个理想主义者时,她叹了一口气说:“很遗憾,不算了。”
与她相比,袁妮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她有了新男友,是初中同学,正在外地读研究生。如果说美中不足,那就是她如今已经不大敢去总爱给他介绍对象的叔婆家做客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袁妮、刘畅、王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