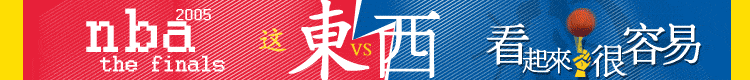有人为母亲擦掉了那颗泪水。我抬起我的手,那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现在,房间里站满了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在哭,或者在拧他们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还在动。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额外的涂油礼后,医生们来了,确认了母亲的去世。
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他已经来到瑞士,离我们不远。他连夜开车赶来,抱住我并且向母亲说再见。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大约10年已经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进房间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时脸上的表情。他握着她的手,然后亲吻了她的额头。对他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一章结束了。
她的遗体在房间内停放了3天。然后,在1月24日清晨,我们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过小村,去往小教堂。我得知在我们这个只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但是他们都沉默着。我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活动—访问索马里的营地时的情景。那里的沉默简直使人觉得失去了听觉。那里有15000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一个人说话。当我们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想象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做。
我曾经努力地想让她笑,这是所有因为单亲而感到悲哀的孩子会做的事情。我会像个小孩儿一样故意做一些滑稽动作,或者用某种可笑的口音跟她说话,然后她就会开怀大笑,有时候甚至会笑得弯腰。她总是拥有敏感而又迟钝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她还在住院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把拜访她的7位医师比作“7个小矮人”。“7个小矮人来过以后,我们将读到某人的来信,或者给某人打电话。”她轻松地说。
她收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信,但是其中一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当她第一次与派拉蒙签订合同以后,她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同业协会的午宴。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重要的位置,挨着马龙-白兰度。大家都坐定后,她感到非常害羞,并向马龙-白龙度问了声好。从此以后,整个宴会上两人再没有说过话。由于母亲和马龙-白龙度的经纪人都是科特-弗林斯,她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科特当时的妻子玛丽。科特几年以前去世了。这对母亲的打击不亚于她的商业经理阿贝-比恩斯托克离开了她。他们彼此都永远存在于对方的生命中,就像家人一样。
玛丽肯定将母亲的话告诉了马龙,包括宴会上的故事以及她的感觉。因为母亲收到了马龙·白龙度的一封信。在信中,马龙-白龙度诉说了他对母亲是多么的敬畏,他又是多么的不善言辞。40年来,母亲一直认为马龙·白龙度是在躲避她,事实上不是那样。他当时只是对母亲肃然起敬,就像母亲对他一样。
她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索马里家庭,他们排着队,平静地等待时不再来的机会。当看到儿童死在他们母亲怀里的情景时,母亲深受伤害。她知道目前人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能够做的也受到各种限制,同时无力阻止不公正和战争的发生,她怎么能够在夜里安然入睡?她怎么能够看着我们在餐桌上,在厨房里嬉闹,享受着天伦之乐从容度过一生?难道这注定了生命开始的分离过程吗?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官在母亲去世之后几个月也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不是人类由于同情和怜悯产生的死去的意志,就像人们想要生存的意志一样强烈?这两者的区别能被人们知道吗?是不是就像随波逐流一样,就像山羊跳下悬崖?
我们走得很缓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锐边缘刺痛我们的肩部。我抬起头看了看太阳,太阳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着。在狗仔队用直升机偷拍的事件发生后,我找来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他是瑞士军队的退役上校。我告诉他直升机事件对母亲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他听着我诉说。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直升飞机在葬礼那天的上空盘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知道。我要求这个一生中从来没有向规则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这里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在那里,这样的奇迹只要有一点政治的干涉就会发生。但是这是瑞士,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他虽然也来参加葬礼了,但是没有给我答复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干净的。我后来得知,上层--我也不知道是多么高的上层--有命令下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把整个葬礼区域设为禁飞区。我微笑着。这次我们终于阻止了狗仔队。在几周寒冷阴沉的天气以后,太阳终于露面了。
仪式简短而又温馨。我最后发言,以下是我说的:
教师、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员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曾经为她写过一首诗。妈妈很喜欢这首诗。今年圣诞节她最后一次读了这首诗。她给这首诗命了名。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