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60年涌现了太多的伟大女性,请你为她投下宝贵的一票。
怀旧老化妆品,评论新化妆品,你童年最爱用的牌子还在吗?
建国60年对时尚产生了什么化学反应?

她还是笑,突然觉得这场相亲会很有意思。他呆呆看她的笑意,慢慢把欣喜写在一双眼睛里。这就是一见钟情吗?回到部队,他忍不住有给她写信的冲动。[我也说说]
姨妈说,妈妈在结婚当天,不想结婚,直接落跑,原因很简单,不想对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在一起,不想过着父母要自己嫁的婚姻。温柔的妈妈竟有这样的一面。[我也说说]
父亲17岁那年,祖母托媒到母亲家提亲。这时母亲16岁。母亲生的俊俏,提亲的人很多,但外祖母都不同意,最后相中了朴实又有文化的父亲。父亲对待岳父岳母如同亲父母。[我也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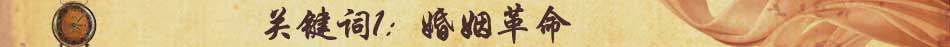
60年过去了,“刘巧儿”仍然会被人提起,这是个曾经蜚声全国的名字,能瞬间唤起父辈们心中那个熟悉的形象。而这个形象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叫封芝琴。
旧社会,有俗话“养女济困”。捧儿爹希望张家多给些彩礼,哪知张家人借着政府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看到两个孩子情投意合,便想省下彩礼钱。
捧儿爹想不过味,一不做二不休,给女儿另许了婆家。捧儿哭得泪人一般,死活不愿意。封父看女儿不愿,就又另寻了一家。当然,捧儿还是不愿,她心里只有一个岁蛋哥。
张父得知封家接连给捧儿找婆家,就以屡卖女儿为名把捧儿爹告上了甘肃省华池县民主政府司法处。司法处作出判断,均以父母包办买卖为由撤销了捧儿的前后三次婚约,没收了所有的彩礼。两家从此产生了隔阂,不再来往。
这场官司惹得封父又羞又恼。他托人四处打听,执意要再给捧儿找个好婆家。没过多久便有了眉目,是户姓朱的人家,人才家道都不错,婚事就这样定下了。[详细][我来说几句]

我叫和慕娟,是沈阳市第一食品厂一名退休工人。1956年8月和老伴蒲文和登记结婚,这张结婚证陪伴我们携手走过了52年的风雨历程。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乐亭县的农村。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坚强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4人艰难的生活。因为家里穷,缺劳力,小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学习的机会,安心在农村参加劳动。
两年后,有亲属在城市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叫蒲文和,是辽宁省建昌县人,当时一见面我就非常喜欢,不仅人长得精神,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而且他的经历是相当不简单。他1947年当兵入伍,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回国。因为在部队表现优秀,回国以后他被派往河北省昌黎县军校学习,我们就是在他学习期间认识的。
在我看来,一个城市人,一个表现优秀的军官,我是那么敬佩他,如果能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详细][我来说几句]

当我们到了热恋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革到了我父亲的头上,他当时是亿盖县四中高中语文教研组长。1948年的一天,上级来人要全校的老师集体填了张加入国民党的表格,没有任何活动。解放后,父母到有关部门登记,当时组织上的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自然把父亲当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开始批斗。
朱凤琴的商店领导闻知她与我处对象,支部书记亲自找她谈话,让她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和国民党的儿子划不清界限,有的还热心地为她介绍解放军干部的对象。她虽然痴心不改,但毕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预备党员还没转正,弄不好还会丢掉“政治生命”。在各种压力下,她出现了失眠的现象,心脏也出了毛病。
当时社会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还很有市场。而凤琴根红苗正,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商店重点培养的接班人。
我父亲每天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被批斗,关在牛棚。[详细][我来说几句]

上世纪80年代末,京城曾经出现一个轰动一时的“秦香莲上访团”。一面红色的小旗上,写着“秦香莲上访团”六个字,小旗旁常簇拥着几十个脸色憔悴、神情忧悒的女人,有的蓬头散发,有的衣装整洁,有的抱着孩子……
这个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团长”是北京人薛桂荣,团员则来自全国各地。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上告她们当了“陈世美”的丈夫。
薛桂荣原本是北京一家服装厂的女工,22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同厂工人黑冠宇。二十多年了,日子尽管不是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却也相安无事。
谁料,年过半百,孩子也快成人了,黑冠宇在家里话却变得越来越少,后来发展到三天两头不着家。
薛桂荣起了疑心,开始做起了“侦探”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来,黑冠宇在外头已经有了相好了。[详细][我来说几句]

李爽躲在法国人白天祥的公寓里。尽管公寓就在北京,她踩着的是自己国家的土地,但她依然有些心里没底。每当有陌生人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她都忍不住一阵紧张。
这是1980年的秋天,李爽刚刚23岁,身份是自由画家,最辉煌的职业经历是参加了中国美术馆的星星画展。“窝藏”她的白天祥是她的情人,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1979年,两人在一次画展中结识,互相欣赏的二人不久后开始交往。这对中法恋人的爱情产生在了“错误的时间”——文革刚刚结束,“错误的地点”——政治气氛浓厚的北京。一个中国姑娘怎么能与老外有密切接触并产生感情?国门刚刚打开,此时的社会风气依旧保守封闭。性格豪爽的李爽在平日就是打眼的人,她本不打算遮掩这段感情,“相爱难道不是一切的理由吗?”但周围人的反对声超出她的想象,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人们对自己指指点点。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有关领导也找到李爽,提醒她“要注意影响”。
后来李爽悄悄搬进其位于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里,成了爱情囚徒。[详细][我来说几句]

男人没有女人就没有家。丁乃钧直到40岁仍然单身一人。
1980年年底的一天晚上,整个学校一片冷清,年近40岁的丁乃钧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一份《人民日报》。无意间,他看到了一则广告,便突发奇想:既然产品能在报纸上登广告,单身的我是否也可以在报上刊登一则征婚广告呢?于是,丁乃钧连夜给《人民日报》的编辑写了封长信,请求给他登一则征婚广告……
1981年初,《市场》报刊登了这则征婚启事,丁乃钧也成了新中国公开征婚第一人。
丁乃钧的征婚启事是这样写的:
“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7米。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
由此,丁乃钧赚取了足够的眼球。“文革”对人性的压抑轰然释放,一颗颗年轻、好奇、爱美的心正在萌发,一个不断产生新奇的时代已经到来。[详细][我来说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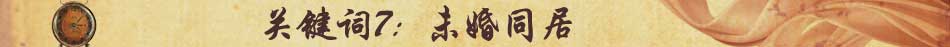
褚芳莲与徐先桃,恋爱始于1976年的秋天。那时候,21岁的徐先桃,是全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幼年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与胞妹相依为命。加之徐弱不禁风,常年患病,亲友们都为他未来的婚事担忧。
不久,经人介绍,徐先桃认识了邻近的昌松公社松山四队褚芳莲姑娘。她身材匀称,眉清目秀。两人一照面,都暗暗相中了对方。8月,两家热热闹闹地将这门亲事订了下来。
同年10月,大学恢复招考的消息传开了,徐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考试。他把这一打算告诉芳莲后,当即得到了她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1978年春,徐先桃被南京某大学录取了。临行前的一晚,他俩一直谈到深夜,互相嘱咐,共表誓言。这一夜,两人突破了最后的防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徐先桃的眼里,婚姻问题也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升腾,在更迭。[详细][我来说几句]

自从被人包养后,泡泡就不再缺钱了。从前那个被我撞翻小拇指吵着闹着要我赔钱的美女不见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位闲散而慵懒的妇人。她养猫养狗种花逛街打牌赌球赌马,就是填补不了心头的虚空。有时,富商回英国探亲两三个月,泡泡便疑神疑鬼,像得了忧郁症。更多的夜晚,她选择向我电话诉苦来疏解伤痛,将一桶又一桶的情感垃圾倾倒在我的心底。
后来,泡泡三更半夜打电话来喊救命,等我发疯般赶到她家时,她竟然跌倒在盛满洋酒、白酒的浴缸里!原来,她为了惩罚那个久未归家的富商,拧开了他家地窖中所有的酒瓶,将洋酒、白酒、葡萄酒统统倒在浴缸里,准备给自己来一个舒筋活血的酒浴。当她把自己扔进昂贵的酒液中时,高浓度的酒液瞬间灼伤了她的肌肤,她一慌神栽倒在浴缸里,久久爬不出来。
我再一次将她送进医院。我知道,无论是医院或者是我,都医治不了她心头的伤。
最后,我毅然决定从此不再接她的电话。我认为这种选择是对的,我的道德感太强,无法承受,不敢面对泡泡的未来,不敢想象一位二奶晚年的孤寂生活。[详细][我来说几句]

著名的《海蒂性学报告》指出在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下,女性外遇的意义,不只在情感和性欲的满足,有些是对丈夫外遇的报复。
蓝菲的故事就是其中的非典型案例。
如果说外遇有主动和被动之分,那么一开始,她属于后者。情感和欲望无处释放,靠和丈夫之外的男人发生纠葛,以图换取些许的自尊和平衡。
自从发现丈夫凌伟明那天晚上并非如他所说,在和部门同事开会之后,心思细腻的蓝菲便发现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对自己说谎。有时谎言说得太逼真,连凌伟明自己都以为是真的。可蓝菲从未当面揭穿,她始终抱着一丝幻想:他只是工作压力太大,需要时间和空间放松。以他们从高中起开始恋爱的牢固感情基础,外面的女人不可能会吸引到他。
可当蓝菲亲眼见到那个穿着“淑女屋”蕾丝裙的大学女孩时,她的大脑只剩一片空白。当时,蓝菲和所有第一次知道丈夫出轨的女人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详细][我来说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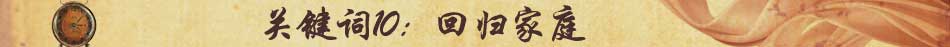
我老婆现在成了她朋友们羡慕的对象:老公对她百般疼爱,一有空就携妻挈子外出旅游、运动,甚至还会带她去听昏昏欲睡的音乐会和看不懂的话剧……女人们说,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外国电影才有的结婚多年仍然恩爱如初,看到了什么叫始终如一。当老婆给我讲述这些的时候,她的表情是满足的、骄傲的、自信的。
谁也不知道,我们也曾有过淡漠的几年,一度差点离婚。
我今年32岁,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受社会风气和内心某个角落欲望的影响,结婚两年时,我出轨了。
现在回头分析当时的心理,我还是能够原谅和理解当时的自己。对那些仍然视婚外感情为时髦游戏的人,我也不会认为他们人品有什么问题,社会已经很宽容了,我也不会那么“卫道士”。但我不会再那样,因为我真正意识到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家庭、我的爱人,我不希望他们难过。[详细][我来说几句]